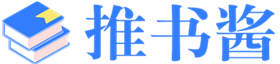简介
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悬疑灵异小说,巡江诡簿,正等待着你的探索。小说中的陈勘角色,将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惊喜和感动的世界。作者择星记的精心创作,使得每一个情节都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现在,这本小说已更新119798字,热爱阅读的你,快来加入这场精彩的阅读盛宴吧!
巡江诡簿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暂时的、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同盟关系虽然勉强达成,但帐篷内外(或者说,此刻我们所在的这个临时空间内外)的气氛,却并未因此而立刻变得轻松或热络起来。张破岳依旧是那副言简意赅、惜字如金的模样,行动迅捷而利落,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经过长期严格训练才能养成的、近乎军人般的精准与效率,没有丝毫多余的拖沓。他迅速地将最后几件散落的工具——包括那卷凯夫拉绳索和复杂的滑轮组——分门别类地塞进对应的装备袋或固定在背包特定位置,然后提起最重的那个银色金属箱,用一个简洁的下巴动作示意我跟上,便率先转身,踏着被晨露打湿的泥土,向着与那片弥漫着不安气息的湖湾相反的方向走去。
我们没有沿着我昨夜亡命奔逃时、那条在芦苇和乱石中磕磕绊绊开辟出的“路径”返回,而是沿着曲折的湖岸线,向着另一侧绕行。大约走了十几分钟,穿过一片更为茂密的、挂着晶莹露珠的柳树林后,一个极其隐蔽的、几乎被肆意生长的水草和低垂柳枝完全遮蔽的简易小码头,出现在我们面前。码头上系着一条看起来饱经风霜的老旧小木船,船身的蓝色油漆已经斑驳脱落了大半,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质纹理,船尾挂着的是一台看起来颇有年头的、型号老旧的单缸柴油舷外机,与张破岳身上那些闪烁着科技冷光的高精尖装备形成了鲜明而突兀的对比。然而,这条船虽然外表朴实无华,甚至有些寒酸,但船体结构看起来却很结实,缆绳系得牢固规范,发动机外壳也被擦拭得干干净净,显然得到了精心的维护。
“上船,坐稳,别乱动。”他言简意赅地吩咐道,声音被发动机启动时那突兀的、如同老人咳嗽般的“突突突”声所部分掩盖。小木船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颤抖起来,缓缓驶离了那个隐蔽的码头,笨拙却又坚定地破开平静如镜、倒映着灰蒙蒙天空的湖面,向着与那片笼罩在迷雾和秘密中的可疑湖湾截然相反的方向驶去。他显然极为谨慎,丝毫没有立刻返回“案发现场”的打算,哪怕那里可能隐藏着关键的线索。
我依言坐在狭窄的船头,双手下意识地紧紧抓住湿滑冰冷的船舷,感受着清晨湖面那带着彻骨寒意的风,像冰冷的刀片一样刮过我的脸颊和耳廓。远处,随着天色渐明,湖对岸那连绵山峦的轮廓在消散的雾气中逐渐变得清晰、硬朗起来,一些早起的水鸟开始活跃,在远处的芦苇荡上空盘旋、鸣叫,划破了黎明的寂静。我的心情如同这被船桨搅动的湖水一般,复杂难言,充满了不真实的恍惚感。就在短短一夜之间,我的人生轨迹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强行扭转,从一个在故纸堆里打转、异想天开的民俗学研究生,一个独自冒险、差点葬身湖底的愣头青,戏剧性地变成了眼前这个身份成谜、行事诡秘、却拥有着惊人专业能力的男人的“临时搭档”或者说“临时累赘”。这种身份的骤然转换,带来的不是兴奋,更多的是一种如履薄冰的忐忑和对未知前路的深深忧虑。
小木船在空旷的湖面上不紧不慢地行驶了约莫二十多分钟,发动机单调的“突突”声成了唯一的节奏。最终,它在另一处更为荒僻的湖岸拐角停了下来,靠近一个看起来像是早已被废弃的、隶属于某个渔业管理部门的小型观测站。那小屋孤零零地矗立在岸边,墙皮剥落,木质窗框腐朽变形,窗户玻璃蒙着厚厚的灰尘和蛛网,一副年久失修、被人遗忘的模样。然而,张破岳却径直走到小屋门前,从工装裤一个隐蔽的口袋里摸出一把略显老旧的黄铜钥匙(他竟然有这里的钥匙!这再次印证了此地绝非他声称的“临时落脚点”那么简单),利落地插入锁孔,轻轻一拧,“咔哒”一声,门应声而开。
屋内的景象与外部破败的外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虽然陈设简单,只有几张行军床、一个旧木桌、几把折叠椅和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柜,但到处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物品摆放井然有序,地面没有积灰,空气中也只有一股淡淡的防潮剂和金属保养油的味道,更像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功能明确的安全屋或者前进基地。
“这里暂时是安全的,平时很少有人来。”他放下沉重的装备,言简意赅地解释了一句,算是回答了我眼中的疑惑。随即,他走到木桌前,从那个银色的金属箱里,取出一台外壳明显经过加固处理、带有军用风格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个同样坚固的便携式移动硬盘。他按下电脑电源键,屏幕亮起,发出幽蓝的光。
“现在,把你昨天在那片湖湾采集的所有土壤和水样,都拿出来。”他转向我,语气不容置疑。
我连忙应声,像是接受检阅的士兵,手忙脚乱地从我那依旧湿漉漉的登山包最底层,小心翼翼地取出那几个承载着我所有冒险代价的玻璃广口瓶和自封袋,双手捧着,递到他面前。
他接过去,并没有像我那样直接上手,而是首先从装备箱的一个小隔层里,取出一副质地更厚、密封性更好的丁腈橡胶手套,熟练地戴上。然后,他在那张旧木桌上铺开一大张干净的、崭新的锡箔纸,这才将我的样本逐一取出,放置在锡纸上。他的观察方式也与我走马观花式的查看截然不同。他先是拿起土壤样本,对着从窗户缝隙透进来的天光,极其仔细地观察其颜色、湿度、颗粒组成,甚至用手指(隔着手套)轻轻捻动,感受其粘稠度和质地;接着,他又将样本凑近鼻尖,短暂而克制地嗅闻了一下,眉头微蹙。随后,他拿起一个只有巴掌大小、却集成度极高的便携式快速土壤检测仪,用附带的小勺子取了极小一撮颜色最深的土壤,放入仪器的检测槽中。
仪器发出极轻微的嗡鸣,屏幕上的数据开始飞速跳动、刷新。几秒钟后,结果清晰地显示出来:“pH值:3.8……硫化物(以S²⁻计)浓度:127 mg/kg……铁离子浓度:显著偏高……”
他看着屏幕上的数据,低声自语,声音低沉而清晰:“pH值显著偏低,呈强酸性……硫化物含量异常偏高,超出湖区背景值两个数量级……这解释了土壤的粘腻感和部分颜色成因。”
接着,他转向水样。他取出一支更精细、探头更复杂的水质多参数检测笔,小心地插入广口瓶中,避免触碰瓶壁。检测笔的屏幕上,数值同样快速变化并最终稳定下来:“溶解氧(DO):2.1 mg/L……电导率:1850 μS/cm……再次检测到硫化物成分……浊度:28 NTU……”
他的眉头随着一项项数据的读出,越皱越紧,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这些冰冷而精确的数字,如同最严厉的法官,毫不留情地印证了那片区域的非同寻常,其异常程度,甚至可能超出了他之前的初步预估。
然后,他转向那台加固笔记本电脑,快速敲击键盘,调出了一系列复杂的图表和数据文件窗口。“这是我之前利用侧扫声纳、浅地层剖面仪以及定点锚系观测设备,在不同时间段,对老爷庙水域,特别是包含你发现异常的那片湖湾在内的区域,进行的水文和地质扫描所获取的初步数据集合。”
屏幕上瞬间被各种我完全看不懂的专业图像所占据:有颜色深浅不一、如同抽象画般的水下地形等高线图;有标注着不同颜色箭头、显示水流方向和速度的流速矢量分布图;还有更加晦涩的、由无数密集波峰波谷组成的声学频谱分析图或地震反射剖面图。我看得眼花缭乱,如同在看天书,只能勉强根据颜色的差异和数值的标注,大致分辨出哪些区域可能代表着“异常”或“不同”。
“重点看这里,”他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困惑,用指尖在触控板上滑动,将其中一幅水下地形三维扫描图放大,并指向图中那片对应着异常湖湾的水下区域。在那相对平坦的湖床上,确实存在一个极其不易察觉的、颜色略深于周边区域的、微弱的凹陷地带,其边界模糊,但仔细看,形态与周围连续的地质背景确实显得有些不协调,仿佛下面掩盖着什么。“这里的水下底床形态,存在轻微的、非自然形成的异常起伏,虽然被厚厚的沉积物覆盖和模糊,但其轮廓暗示下方可能存在一个局部结构体或者空腔,与周围的地质构造连续性不符。”
他又快速切换到另一幅由计算机模拟生成的水流动态矢量图。图中,大部分区域的水流箭头都指向明确,符合主流风向和湖盆地形的影响。然而,就在那片异常湖湾对应的水域,却存在一个非常微弱的、几乎难以察觉的、持续存在的、小范围的涡旋状扰动流场,其旋转中心恰好与地形图中的凹陷区域大致重合。“再看水流的模拟情况,”他指着那个微小的涡旋,“这里存在一个持续性的、非常隐蔽的涡旋状扰动。它的尺度和强度都很小,不像是由湖面风应力或者大型地形突变引起的常规涡流,更像是由水下某个局部点源的、持续向上的能量或物质释放所驱动形成的。”
接着,他做了一个让我呼吸几乎停滞的动作。他拿起我放在桌角的那几页《巡江见闻录》手稿打印纸,翻到那张描绘着老爷庙水域、画着一个歪歪扭扭螺旋标记的潦草草图那一页,将打印纸上那个代表“水纹涡旋”的、如同孩童涂鸦般的标记,与电脑屏幕上那幅精确的水流动态模拟图中,那个微弱却真实存在的涡旋扰动区域,并排放在了一起,进行比对。
接下来发生的,堪称奇迹般的对应!
手稿草图上,那个用颤抖而急促的笔触画下的、代表异常漩涡的潦草螺旋标记,其所处的大致方位、甚至其螺旋内收的粗略形态,竟然与电脑屏幕上,那由无数精密传感器数据和复杂流体力学算法模拟出来的、代表着水下微弱扰动的涡旋区域,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高度重合的状态!
我猛地瞪大了眼睛,瞳孔因为难以置信而收缩,嘴巴微微张开,几乎要发出惊呼,却又被一种巨大的震撼扼住了喉咙。这……这怎么可能?!几百年前,某个连名字都未曾留下的巡江司底层小吏,或许仅仅是依靠着肉眼观察湖面水纹的细微变化,依靠着手中那根探水深浅的竹竿所感受到的微弱拉力,凭借着最原始的经验和直觉,在那盏如豆的油灯下,用粗糙的笔墨,歪歪扭扭记录下的一个“水纹涡旋”的标记……其指向的位置和形态,竟然在数百年后的今天,被现代最精密的声纳探测技术和复杂的计算机流体模拟,几乎分毫不差地验证、还原了出来!时空仿佛在这一刻被压缩、折叠,古人那充满敬畏与不安的观察,与现代科技冰冷理性的探测,跨越了数百年的鸿沟,在此刻形成了无声却振聋发聩的共鸣!
“还有你之前反复提及,并且亲自感受到的‘异色’和那股‘酸腥’气味,”张破岳的声音将我从巨大的震撼中拉回现实,他指着水质检测数据中那刺眼的低pH值和高硫化物指标,“强酸性环境,加上浓度异常的硫化物(很可能以硫化氢形式存在),这两者结合在一起,完全足以导致水体视觉上的浑浊、颜色发暗或呈现不正常的色泽(比如泛黄、泛黑),并且,硫化氢气体本身,就带有典型的、类似于腐败鸡蛋的刺鼻酸腥气味。古人缺乏现代化学知识,无法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只能根据最直接的感官体验,将其记录为‘异色’、‘腥臭’,并基于当时的认知水平,归因于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泄毒’。”
冰冷的、精确的现代科学检测数据,与古老、模糊却充满现场感的手稿文字记载;古人基于经验的朴素观察,与现代依靠仪器进行的定量测量——这两条原本看似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在此刻,在这个偏僻破旧的小屋里,竟然形成了如此完美、如此令人信服的交叉验证!每一个疑点,每一个异常,都找到了对应,构成了一个逐渐清晰的、令人不安的图景。
我们两人都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小屋之内,只剩下那台加固笔记本电脑散热风扇发出的、持续而轻微的“嗡嗡”声,如同背景噪音般填充着这震撼过后的寂静。一种难以言喻的、混合着发现真相的激动与对未知危险的深切忧虑的复杂情绪,在我们之间无声地弥漫、发酵。这不再是我个人的臆测或巧合,也不再是张破岳单方面的专业怀疑。这是被来自不同时空、不同维度的证据,共同、反复指证的一个确凿无疑的异常点!那片看似平静的湖湾之下,确实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持续活动的秘密!
“看来,”张破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这沉重的事实吸入肺中,他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甚至带着一丝凛然,“我们之前的所有推测,可能都还是过于保守和乐观了。那里存在的,恐怕远远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工业污染渗漏点,或者一个单纯的地质化学异常现象。”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铺着锡纸的桌面上,一遍又一遍地、缓慢而有力地描画着那个代表水下涡旋的螺旋形状,目光却仿佛穿透了这破旧小屋薄薄的墙壁,投向了窗外那浩瀚无垠、深不可测的湖面,仿佛要凭借意志力,穿透那数十米深的、浑浊冰冷的湖水,直视那隐藏在一切异常之下的、被时光掩埋的终极真相。
“那里,可能真的存在一个……一个‘穿穴’。”他低声说道,声音不大,却像一块投入深井的石子,在我心中激起了巨大的、久久不散的涟漪。这一次,他的语气不再带有任何假设或推测的意味,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已经被多方证据所共同证实了的、冷酷的既定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