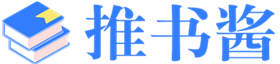简介
今天要推的小说名字叫做《巡江诡簿》,是一本十分耐读的悬疑灵异作品,围绕着主角陈勘之间的故事所展开的,作者是择星记。《巡江诡簿》小说连载,作者目前已经写了119798字。
巡江诡簿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决心一旦像颗生锈的钉子被硬生生敲进木头,便似乎再无回头路可走。或者说,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以及前期已经投入的、足以让我肉痛好几天的“沉没成本”——比如打印费、资料查询耗费的时间精力,以及那点被勾起来就再也按不下去的好奇心——也不允许我像个临阵脱逃的新兵一样,轻易地举起白旗。
接下来的两天,我彻底化身为一只为即将到来的严冬而疯狂囤积食物的松鼠,忙碌、琐碎,甚至带着点神经质地在宿舍和学校周边奔波,筹措着这次被我内心戏称为“孤身远征”的行动。首要的,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资金。我反复点开手机上的银行APP,盯着那串可怜巴巴、仿佛随时会断气的数字,感觉它不是在显示余额,而是在为我鸣奏一曲凄凉的哀乐。内心经过一番激烈的、堪比菜市场讨价还价的挣扎后,我最终还是咬紧后槽牙,手指带着一丝悲壮的情绪,在购票软件上按下了确认键,预订了那趟传说中的“绿皮神车”——一趟需要在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时就出发,沿途停靠无数小站,晃晃悠悠耗费近六个小时才能抵达目的地的硬座车票。支付成功提示音响起的那一刻,我清晰地感觉到,我那本就干瘪的钱包灵魂,又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体积肉眼可见地萎缩了一大圈。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清晰无比的、源自生理层面的肉痛。
如果说资金问题是沉重的现实打击,那么装备采购过程,则直接将“业余”和“临时抱佛脚”这几个大字,用加粗字体刻在了我的脑门上。我没有,也根本买不起任何专业的土壤或水体取样器。在搜索引擎的临时抱佛脚指导下,我硬着头皮走进一家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化学试剂店。店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酸味和塑料味,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奇形怪状的玻璃器皿和化学药品,让我这个文科生感到一阵莫名的紧张。我尽量让自己显得像个内行,指着柜台里几种不同规格的玻璃瓶,对那位戴着老花镜、正在看报纸的老板说:“要几个……带螺纹密封盖的广口瓶,嗯,还有那种厚实点的,密封性好的聚乙烯塑胶袋。”
老板从镜片上方抬起眼皮,慢悠悠地打量了我一番,那眼神仿佛在判断我是不是哪个中学偷跑出来搞恶作剧的学生。“做实验用?”他随口问道,声音带着点沙哑。
我心里咯噔一下,虚得像是偷了东西被当场抓住,含糊地“嗯”了一声,连忙补充道:“就……学校布置的,简单取样。”天知道,我这算哪门子实验?连实验目的和方案都模糊得像隔着一层毛玻璃。
最终,我提着几个100ml和250ml的棕色玻璃广口瓶、一叠厚实的高密度聚乙烯自封袋、一盒看起来质量尚可的一次性PVC手套,以及一包普通的医用外科口罩(这大概是我能想到的、最基础的,也是心理安慰作用大于实际防护效果的“防护”了),几乎是逃也似的离开了那家店。老板那探究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背上。
回到宿舍,我开始清点我的“冒险者行囊”或者说“破烂收藏”。我的“武器库”堪称寒酸且充满混搭风:那台陪伴我多年,外壳已经有些掉漆、镜头在光线不足时对焦会发出令人尴尬的“吱吱”声的旧数码相机,我反复检查了内存卡和电池,祈祷它关键时刻别掉链子,希望能清晰记录下任何可能的关键景象;一支上民俗田野调查课时,学校统一配发的黑色录音笔,样式古板,但续航能力意外地不错,或许能用来记录现场的环境音和我的即兴观察;一个A5大小、牛皮纸封面的硬壳笔记本,以及几支红蓝黑三色的签字笔,准备用于现场素描(如果我那蹩脚的画技能支撑的话)和详尽的文字记录;一个多年前受武侠小说影响,一时冲动在旅游景点买的、带有水平仪和方位刻度的仿古金属罗盘,黄铜外壳已经有些氧化发暗,此刻竟成了我所有装备里看起来最具“专业性”和“仪式感”的物件,尽管我对其使用的准确性深表怀疑。
除此之外,还有诸如充电宝(确保手机和录音笔不断电)、一小卷透明胶带(万能修补工具)、一小瓶免洗洗手液(心理洁癖作祟)、几块味道寡淡但能提供热量的压缩饼干,以及一瓶最普通的矿泉水。所有这些东西,被我分门别类、又略显杂乱地一股脑塞进那个跟随我走南闯北多年、深蓝色帆布面料已经磨损发白、边角甚至有些开线的登山包里。这个包承载过我本科时下乡调研的尘土,也装过考研时的复习资料,如今,它又要陪我去进行一场前途未卜的探索。
打包完毕,我双手用力,将沉甸甸的登山包提起来掂了掂分量,不算轻,肩膀已经能预感到几个小时硬座旅程后的酸痛。但一种奇异的感觉也随之涌上心头,混杂着一点点筹备就绪的踏实感,和更多自我营造的悲壮感。仿佛我不是要去验证一个可能毫无意义的古老记录,而是像那些传奇故事里的主角一样,要去完成一项关乎某种隐秘真相的秘密使命。这种略带中二色彩的自我暗示,像一针效果微弱的兴奋剂,多少冲淡了一些经济上的窘迫和对未知前路的忐忑。
出发前夜,宿舍里依旧只有我一个人。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光透过没拉严实的窗帘缝隙,在天花板上投下模糊的光斑。我再次坐到电脑前,像战前最后一次检阅地图的指挥官,最后一次核对所有“情报”。屏幕上并排显示着两个窗口:左边是那页《巡江见闻录》手稿的扫描件,歪歪扭扭的线条和潦草的字迹,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右边则是从某个旅游网站上下载的老爷庙水域全景照片,像素很高,画面里是宽阔平静的湖面,现代化的航标灯塔矗立水中,远处隐约可见修建整齐的堤岸和一些旅游设施,一片祥和安宁的现代景象。
手绘的抽象草图,与现实清晰的航拍图,形成了近乎荒诞的强烈反差。古人笔下那充满危机感的“凶”地,在现代技术的俯瞰下,显得如此普通,甚至有些乏味。这种视觉上的冲击,像一盆冷水,再次将我从自我营造的悲壮氛围中浇醒,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自我怀疑:陈勘,你是不是疯了?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一个虚无缥缈、大概率是古人臆想或误解的线索,耗费本就拮据的金钱和宝贵的精力,像个傻子一样跑到一个旅游景点去“考察”?或许导师李教授才是对的,我确实被猎奇心理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蒙蔽了理智,正在一条毫无学术价值、纯粹是浪费时间的不归路上狂奔。
烦躁和犹豫像潮水般涌来。我几乎要伸手关掉电脑,把登山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然后明天早上乖乖地去图书馆,继续我那关于水工祠的、虽然枯燥但至少安全的论文写作。
但就在我的手指即将触碰到鼠标的那一刻,目光再次划过屏幕上那行手写的字迹——“疑有穿穴泄毒”。那歪斜的笔画,仿佛带着书写者当时的一丝惊惧或笃定。那种微妙的、被某种可能性勾连起来的感觉,如同黑暗中一点极其微弱的星火,再次在我心底固执地闪烁了一下。
哪怕,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呢?哪怕最终证明一切都只是我的臆想和巧合,现场毫无异状,我只是白跑一趟,像个十足的傻瓜。但至少,我行动了。我走出了这个堆满故纸堆的房间,亲自去验证了。这本身,或许就比永远困在无休止的猜测、犹豫和自我否定里,要强上那么一点点。行动,本身就是对停滞生活的一种反抗,哪怕这反抗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
这个念头,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倒了摇摆的天平。
我长长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要将宿舍里浑浊的空气和所有纷乱的思绪都吸入肺中,再缓缓吐出,试图平复那颗在胸腔里有些紊乱、砰砰直跳的心脏。然后,移动鼠标,点击了关机。
屏幕暗下去,房间陷入更深的昏暗。
明天,当黎明的第一缕曙光还未照亮大地的时候,我便会独自一人,背负着那个装满了各种“业余”装备的登山包,毅然决然地踏上那趟陈旧的绿皮火车。这趟列车将带我穿越城市的喧嚣和繁华,驶向那片神秘而令人心悸的水域。
这片水域,在数百年前曾被某个无名小吏标注为“凶”。它的名字或许早已被人们遗忘,但那个“凶”字却如影随形,让这片水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我对它的了解仅限于此,然而正是这种未知,让我对它充满了无尽的好奇和探索的欲望。
火车缓缓驶出站台,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在寂静的凌晨显得格外清晰。我静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凝视着窗外逐渐模糊的城市夜景,心中却早已飞到了那片遥远的水域。
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是印证我所有隐秘期待和推论的惊人发现,还是毫无悬念、平淡无奇的现实,最终证明我陈勘,不过是个被故纸堆逼疯了的、一厢情愿的傻瓜?
无论如何,箭已离弦,再无回头路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