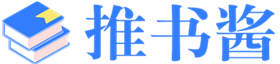简介
石语新墙是一本备受好评的历史古代小说,作者静之行者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小说的主角陈三阿杰勇敢、善良、聪明,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已经完结引人入胜。如果你喜欢阅读历史古代小说,那么这本书一定值得一读!
石语新墙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上篇):工造司的日常
凤凰城工造司的廨署,并非官衙的森严格局,反倒更似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匠作作坊。时辰刚过卯时,坊院内已是声浪叠涌。
空气里炖着一股浓稠的、几乎能摸出纹理的复合气味:新剖开的青冈木带着清冽的甜香,大漆的郁烈中掺着一丝氨水的锐利,石粉的干呛,桐油的醇厚,以及从角落里那尊永远咕嘟着牛皮胶的小铜锅里弥散出的、带着皮肉腥气的粘腻暖雾。各种气息绞缠在一起,沉甸甸地压下,又被窗外灌入的晨风搅动,形成一种独此一家的、令人心神稍定又隐隐亢奋的“活气”。
在这片声浪与气味的海底,算盘珠子的撞击声是永不停歇的底噪,清脆、密集、不容置疑,如同丈量着所有创造物的价值边界。
邵工造便端坐于这片海底的正中。
他面前是一张被各种工具样本和账簿册子吞没了大半的柏木大案。案角,一盏黄铜灯盏里,菜籽油的灯火苗细小而稳定,将他握着紫毫笔、正在一册泛黄的《物料流水账》上勾勒的侧影,投在身后一架顶天立地的多宝格上。格子里分门别类塞满了东西:不是古玩,而是各色石料、木料、漆料、胶料的样本,每一块都贴着小小的墨书签条,像一座沉默的物性图书馆。
他书写时,眉心拧着一道深深的竖纹,并非不悦,而是全然的专注。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与窗外凿石的叮当声、院内锯木的嘶哑声,奇异地应和着同一节奏。
忽地,他书写的动作一顿。笔尖悬停半空。
他并未抬头,只伸出左手,精准地从案头一堆待验的石料中拈起一块灰扑扑的砂岩石板。石板不过巴掌大小,二指来厚。他用指腹缓缓摩挲过石面,然后屈起中指,以指节叩击石板边缘。
“咚。”声音沉闷,短促,毫无余韵。
邵工造花白的眉毛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他将石板凑到灯盏旁,眯眼细看其侧面肌理,又用指甲在石面一道极细微的天然裂隙处轻轻刮擦。
随即,他手腕一沉,将那石板毫不迟疑地丢进脚边一个专盛废料的粗陶大缸里。
“砰”的一声闷响。石板应声裂成数块,断面处露出内部酥松发糠、颜色黯淡的质地。
“声音发闷,内里已糠。”他低声自语,像是说给一旁的书记员听,又像是说给自己听,“受力必从芯子里崩。不堪大用。”
整个过程不过息间,他始终未曾抬眼,右手紫毫笔再度落下,在账册上该石料编号后,利落地批下两个字:“弃用”。
笔锋刚健冷硬,与他判决那块石料的语气一般无二。
(中篇):流光迷梦
一道纤长的影子,被晨光投在邵工造那册《物料流水账》的纸面上,微微晃动。
邵工造无需抬头,便知是谁。那影子带着少年人特有的、介于凝滞与躁动之间的微妙张力。
他的儿子,邵寒。
少年邵寒并未像其他工匠那般穿着便于劳作的短褐,而是一身浆洗得十分挺括的青色棉布直裰,领口袖缘一丝不苟。他安静地立在父亲案旁几步远处,像一株被精心修剪过的幼松。目光却并未落在父亲笔下的账册,或是那些等待判决的石料样本上。
他的全部心神,都被父亲案头一角,那块刚从西山新矿坑呈送来的试样石牢牢吸摄。
那石块不过拳头大小,却通体流转着一种奇异的、近乎活物的光泽。底色是沉静的墨黑,然则在不同的光线角度下,内里却迸射出细密如蛛网的金色与绛紫色星芒,仿佛将一片微缩的星空,囚禁在了冰冷的石壳之中。这便是工造司新近痴迷,意欲大力推广用于城主府邸装饰的“流光石”。
邵寒看得有些痴了。他甚至无意识地微微屏住了呼吸,右手虚抬,指尖在空气中极其轻微地颤动着,仿佛正隔空摩挲那冰凉光滑的石表,勾勒那璀璨星脉的走向。
他眼中燃烧着一种与他年龄稍显不符的、纯粹而炽热的迷恋。那并非孩童对珍稀玩物的好奇,而更像一个信徒凝视神迹般的虔诚与悸动。这石块在他眼中,不是待验的材料,而是美的化身,是能点化凡俗、创造神异的灵物。
邵工造批完了最后一笔,搁下紫毫笔,发出轻微的“嗒”一声。
这微响却惊动了邵寒。他猛地回神,察觉到自己的失态,白皙的脸颊上迅速掠过一丝薄红。他迅速收敛了目光,垂下眼睑,恢复成那副恭谨少年的模样,只是交握在身前的手指,仍因内心的激动而微微蜷缩。
邵工造这时才缓缓抬起头,目光先是扫过儿子那强作镇定的脸,随后,沉静地落在那块流光石上。他的眼神里没有迷恋,没有惊叹,只有一种审慎的、近乎严苛的打量,如同之前审视那块砂岩石板。
他伸出手,将流光石拿起,掂了掂分量。又从案头抽出一柄乌木柄的尖头小锤,其锤头仅如黄豆大小。
在邵寒几乎要出声阻止的惊悸目光中,邵工造手腕极轻地一抖,小锤精准地敲击在流光石一处不显眼的边缘。
“叮——”
一声极其清越、带着些许金属质感的脆响,在喧嚣的工坊背景音中,刺出短暂而锐利的一瞬。
邵工造凝神静听那声响的余韵,眉头却并未舒展。他转而将石块凑到鼻尖,极其轻微地嗅了嗅。
随即,他将石块放回原处,目光重新看向儿子,沉默了片刻,方才开口,声音平稳无波:
“声脆而浮,如击空瓠。金紫纹路,艳则艳矣,然过于跳脱,失之沉稳。更兼……”
他顿了顿,指尖点了点方才敲击之处那几乎看不见的微小印记。
“石性带一丝阴寒潮气,遇大温差恐生暗裂。华彩在外,筋骨却未可知。尚需……长久勘验。”
每一个字,都像一块冷硬的石头,砸在邵寒刚刚燃起的热切之心上。少年眼中的光,一点点黯淡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隐忍的、近乎屈辱的不解与不服。他无法理解,父亲为何对这般造物的神迹如此吝于赞美,甚至……充满怀疑。
在他看来,父亲那套“听声辨质”、“观纹察理”的老法子,在这天赐的华彩面前,显得如此迂腐、笨拙,甚至……可憎。
邵工造说完,便不再看那石头,也不再看儿子,重新提笔,在账册上记下几笔,却是:“西山新坑流光石,样本一。色绚,声脆,微潮。待深究。”
批语谨慎,甚至带一丝保留的希冀,但与邵寒所期待的激赏,相距何止万里。
少年抿紧了唇,将那份不服与热望,更深地埋进了心底,如同将一颗炽热的火种,摁入了冰冷的灰烬。
(下篇):骨相之争
午后日光西斜,将工造司院内的尘埃照得纤毫毕现。声浪稍歇,算盘声也稀疏下来,唯有那炖煮皮胶的小铜锅,仍不知疲倦地吐着细密的气泡,散发绵长而腻人的香气。
邵工造罕见地离开了他的柏木大案,负手立于院中一排新到的金丝楠木枋料前。这些木材将用于城主书房的重葺,至关重要。他伸出粗糙的手掌,一遍遍抚过木材的截面,感受着木纹的致密与油润。偶尔俯身,仔细嗅闻木材心材特有的、清甜中略带辛辣的“楠香”,以此判断其油性与耐腐年限。
少年邵寒跟在他身后半步,保持着恭顺的距离,心思却显然不在此处。他的目光仍会不由自主地飘回廨署方向,仿佛能穿透墙壁,看到案头那块流光溢彩的石头。
“寒儿,”邵工造并未回头,声音沉缓,“可知为何舍近求远,不用城西林场的柏木,反用这昂贵数倍的蜀中楠木?”
邵寒怔了一下,迅速收敛心神,垂首应道:“回父亲,柏木虽坚,木纹粗直,易翘易裂。金丝楠木性稳,纹美,耐腐,气韵华贵,方配城主府邸。”
回答标准,如同背诵典籍。
邵工造缓缓点头,却又缓缓摇头。他转过身,目光如两盏冷烛,照定儿子:“只答对一半。柏木易裂,是其骨相不足。楠木性稳,是其骨相绵韧悠长。世间万物,石也罢,木也罢,人也罢,皆有其骨相。华彩在外,不过皮囊。支撑百年风雨,抵御蛀蚀蠹朽的,永远是内里的筋骨。”
他抬手,指向院内那些忙碌的工匠,指向那些堆积如山的物料:“工造之责,首在辨骨相,识肌理。知其所能,更知其不能。而后因材施用,扬长避短。纵是凡石陋木,用得其所,亦能负千钧,立百年。纵是金玉之材,置于潮暗蚁穴,亦会朽烂成泥。”
“父亲教诲的是。”邵寒低声应道,指尖却在袖中微微蜷紧。
邵工造凝视他片刻,忽问:“若以那流光石,嵌于书房影壁,你待如何?”
邵寒眼中瞬间焕发出神采,几乎不假思索:“其石光华万千,若能以精工研磨,拼嵌成山水日月之图,辅以金线勾勒,入夜后只需一盏灯烛,便可满室生辉,流光溢彩,必成凤凰城独一无二的奇景!”
他描述得神采飞扬,仿佛那华彩之境已在眼前。
邵工造却沉默地听着,待他说完,目光掠过儿子兴奋的脸庞,最终落回那排沉稳的金丝楠木上,淡淡道:“是奇景。然后呢?”
“然后?”邵寒一愣。
“石性未明,阴寒未除。嵌于室内,若遇地潮,或冬日炉火炙烤,冷热交攻,华彩之下,暗裂已生。不过三五年,轻则光泽黯淡,纹路崩散,重则……砰然碎裂。到时,满室辉光,碎成一地狼藉。这独一无二的奇景,又该如何?”
邵寒脸颊的血色瞬间褪去,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他脑海中那幅华美的图景,被父亲冷硬的言语击得粉碎,只剩下一地冰冷的、尖锐的碎片。
“工造之道,不是炫技,不是逐艳。”邵工造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沉重,敲在邵寒的心上,“是权衡,是取舍,是敬畏。是对物料骨相的敬畏,也是对天地规律的敬畏。一招不慎,耗尽民力民财事小,若致墙倾屋塌,伤人害命……你我父子,便是千古罪人。”
他说完,不再多言,转身继续检视木材。留下邵寒独自站在原地,阳光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少年垂在双侧的手紧紧握成了拳,父亲的话语像冰冷的雨水浇灭了他眼中的火,却未能熄灭那深埋的、对那眩目华彩的渴望与不甘。
他心中甚至冒出一个逆反的念头:父亲是否太过保守怯懦?为何不能是人定胜天,以精妙工艺克服物性缺陷,而非一味地顺应与畏惧?
这无声的诘问,像一道悄然裂开的缝隙,横亘在了父子之间,也横亘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工造哲学之间。
院角,那炖胶的铜锅,发出一声沉闷的“咕嘟”声,如同一声叹息。
(第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