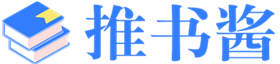简介
如果你正在寻找一本充满奇幻与冒险的历史脑洞小说,那么《逍遥六皇子的传奇人生》将是你的不二选择。作者“海天一色丽人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关于赵宸翊苏清欢的精彩故事。本书目前已经连载,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
逍遥六皇子的传奇人生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一、金殿领旨,剑指江南漕弊
大雍章和七年暮春,长安城内的柳絮刚飘尽,太极殿的朝会便透着一股不同寻常的凝重。赵宸翊穿着靖安侯的绯色常服,站在勋贵列末,目光落在御案上那叠厚厚的奏折上——昨夜林缚已从吏部递来消息,江南漕运接连三个月递上“漕粮足额抵京”的奏报,可苏州、扬州的百姓密信却雪片般送进御史台,说漕船十艘有九艘掺沙,连京畿的军粮都掺了霉米。
“诸卿,”御座上的章和帝放下朱笔,声音沉得像浸了水的铅,“江南漕运,乃国之粮仓。去年黄河抢险,赵宸翊在关中能让农户多收两成粮,如今江南漕粮出了纰漏,谁愿替朕去查?”
朝臣们你看我我看你,没人应声。江南漕运总督冯承业是二皇子赵宸渊的岳家舅舅,扬州知府柳文彦是冯承业的门生,盐商总商沈万山更是年年给二皇子府送百万两白银——这潭水太深,没人愿意得罪二皇子。
“臣请旨。”赵宸翊往前一步,绯色衣袍在晨光里晃出沉稳的弧度,“臣在关中时,曾听西域商队说江南漕船‘载盐不载粮’,愿往江南查漕,还百姓一个公道,还朝廷一个清明。”
章和帝眼中闪过一丝赞许。他早知道赵宸翊敢做事、能做事,只是没想到他敢在这时候接下这烫手山芋。“好!”皇帝拍了下御案,“朕赐你尚方宝剑,便宜行事,可先斩后奏。林缚、周虎、宋平、王河生,随你同去——你的幕僚馆懂实务,正好帮你查弊。”
散朝后,赵宸翊在宫门外拦住林缚。“冯承业是二皇子的人,这次去江南,怕是不止查漕这么简单。”他压低声音,指尖捏着尚方宝剑的剑穗,“你把关中农桑署的账册整理一份带上,就说要跟江南的漕粮账册比对,免得冯承业起疑。”
林缚点头:“殿下放心,昨夜我已让宋平把律法署的断案卷宗也带上了——江南地方官要是敢阻挠,咱们就用律法压他。对了,王河生说漕运跟水利分不开,他想带几套测量漕船吃水的木尺,说不定能用上。”
两日后,赵宸翊一行十余人,乘着一艘不起眼的乌篷船,沿渭水入黄河,再转京杭大运河往江南去。船过淮安时,王河生站在船头,指着远处一队漕船皱眉:“殿下,您看那些漕船——船帮上写着‘漕米百石’,可吃水线比空载还浅,这里面肯定没装多少粮。”
周虎顺着他的手指望去,果然见漕船轻飘飘地在水面上滑,船工们拉纤时脚步虚浮,一点不像载了重物的样子。“要不俺去问问船工?”他撸起袖子,就要跳上旁边的漕船。
“别冲动。”赵宸翊拉住他,“冯承业在淮安关肯定有眼线,咱们一暴露,后面的事就难办了。林缚,你让人去码头的茶摊逛逛,听听脚夫们怎么说。”
林缚应下,换了身粗布长衫,带着两个幕僚馆的文书去了茶摊。半个时辰后,他匆匆回来,手里攥着半块发霉的粟米饼:“殿下,脚夫说这是漕丁偷偷卖的‘军粮’——漕船上的好粮都被换成了私盐,剩下的掺沙霉米,就用来充数。而且每次漕船过淮安关,冯承业的人都会提前给关吏塞银子,连舱门都不开就放行了。”
赵宸翊接过粟米饼,指尖碾开,沙子簌簌往下掉。“好粮换私盐,霉米充军粮……”他冷笑一声,“冯承业胆子不小,连军粮都敢动。王河生,你测算下,一艘‘百石漕船’要是装私盐,能赚多少?”
王河生蹲在船边,用木尺量了量漕船的吃水深度,又在地上画了个简图:“殿下,漕船的舱容固定,百石漕米能换八十石私盐。江南私盐一斤卖五文,官盐一斤十文,盐商把私盐运到北方,一斤能赚三文,一艘船就能赚近五百两——十艘就是五千两,这还只是一次。”
赵宸翊的指节捏得发白。五千两,够关中一个村落的农户吃两年。“看来这漕运的贪腐,比咱们想的还严重。”他站起身,望着江南的方向,“到了苏州,咱们先暗访,再找机会拿证据。”
二、苏州暗访,初窥漕盐勾结
七日后,乌篷船抵达苏州码头。码头上桅杆如林,漕船密密麻麻地泊在岸边,脚夫们扛着粮袋往来穿梭,看似繁忙,可赵宸翊一眼就看出不对劲——粮袋轻飘飘的,脚夫扛着不费力,而且袋口露出的“漕米”,颜色发暗,还掺着碎草。
“殿下,冯承业派人来接了。”周虎凑过来,压低声音,“为首的是苏州通判张启,说是冯总督在寒山寺设了宴,为咱们接风。”
赵宸翊挑眉。他刚到苏州,冯承业就知道了,显然是早有准备。“走,去赴宴。”他整理了下衣袍,“正好看看冯承业想耍什么花样。”
寒山寺旁的望江楼里,冯承业早已等候多时。这位漕运总督穿着一身孔雀蓝的官袍,肚子滚圆,见赵宸翊进来,立刻起身相迎,脸上堆着笑:“靖安侯大驾光临,江南漕运上下真是蓬荜生辉!来,快请坐,这是苏州的鲈鱼,刚从太湖捞上来的,您尝尝。”
赵宸翊坐下,目光扫过满桌的珍馐——清蒸鲈鱼、蟹粉豆腐、冰糖炖燕窝,光是这桌菜,就够普通百姓吃半年。“冯总督倒是好兴致。”他夹了一筷子鲈鱼,慢悠悠道,“只是本侯在路上听说,苏州的漕丁们,连发霉的粟米都吃不饱,不知冯总督知不知道?”
冯承业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如常:“侯爷说笑了。漕丁们辛苦,本督每月都给他们加俸禄,怎么会吃不饱?怕是有人造谣,想挑拨咱们漕运衙门和百姓的关系。”
“哦?”赵宸翊放下筷子,从袖中掏出那半块粟米饼,放在桌上,“那这掺沙的霉米饼,是本侯凭空捏造的?”
桌上的气氛瞬间凝固。张启端着酒杯的手顿在半空,额头渗出细汗。冯承业的脸色沉了下来,却还是强装镇定:“侯爷,这米饼来历不明,可不能随便栽赃漕运衙门。江南漕粮都是按律征收、运输,每一步都有账册记录,侯爷要是不信,本督可以让人把账册拿来给您看。”
“账册就不必了。”赵宸翊站起身,“本侯此次来江南,是为了查漕粮,不是为了看账册。明日起,本侯要亲自去码头查验漕船,冯总督不会阻拦吧?”
冯承业心里暗骂,面上却不敢拒绝:“侯爷是奉旨查漕,本督自然配合。只是漕船众多,侯爷要是需要人手,尽管跟本督说。”
“不必了。”赵宸翊转身就走,“本侯的人,够用。”
回到乌篷船,林缚早已等候在舱内。“殿下,方才我让人去查了苏州的粮仓,”他递过一张纸条,“账册上写着‘存粮五十万石’,可看守粮仓的老卒说,实际存粮不足二十万石——剩下的三十万石,说是‘受潮霉变,就地销毁’,可老卒没见过销毁的痕迹。”
“受潮霉变?”赵宸翊冷笑,“冯承业倒是会找借口。宋平,你怎么看?”
宋平从卷宗里抬起头,推了推鼻梁上的木簪(他没戴官帽,用木簪束发):“殿下,按大雍律,漕粮霉变需有三名以上官员在场查验,还要有销毁记录。冯承业只说‘就地销毁’,却拿不出记录,显然是撒谎——那三十万石漕粮,多半是被换成私盐了。”
王河生也点头:“没错。苏州到扬州的漕道,上个月刚疏通完,漕船通行顺畅,根本不会有‘受潮霉变’的情况。而且粮仓的通风设施都是新修的,漕粮存半年都不会坏。”
赵宸翊走到船窗边,看着夜色里的苏州码头。冯承业的账册是假的,粮仓是空的,漕船装的是私盐——这一切都指向漕官和盐商的勾结。“明日起,咱们分两路查。”他转过身,目光落在众人身上,“林缚,你带文书去查漕运衙门的旧账,重点看近三年的‘损耗率’;宋平,你去苏州府衙,查‘漕粮霉变’的卷宗,看看有没有漏洞;王河生,你跟我去码头,查验漕船的实际载货;周虎,你带护卫暗中盯着沈万山的盐铺,看看他们什么时候跟漕船交接。”
众人领命,各自散去。赵宸翊看着窗外的月亮,手指在桌案上轻轻敲击——他知道,明日的查验,冯承业肯定会做手脚,想要拿到证据,还得从长计议。
三、码头验船,识破障眼法
次日清晨,苏州码头刚热闹起来,赵宸翊就带着王河生和几个幕僚馆的文书来了。冯承业早已等候在码头,身边跟着十几个漕运衙门的吏员,还有几艘“特意挑选”出来的漕船。
“侯爷,这是本月要运往京城的漕船,”冯承业指着最前面的一艘漕船,“您要是想查验,就从这艘开始吧。”
赵宸翊没说话,径直走上漕船。船舱里堆着满满的粮袋,袋口敞开,里面是颗粒饱满的粟米,看起来没什么问题。王河生蹲下身,抓起一把粟米,放在鼻尖闻了闻,又用手指捻了捻,眉头皱了起来。
“冯总督,”王河生站起身,声音洪亮,“这粟米是刚换的吧?”
冯承业脸色一变:“老丈这话是什么意思?这都是按律征收的漕粮,怎么会是刚换的?”
“按律征收的漕粮,存放半个月,会有淡淡的米香,”王河生把粟米递到冯承业面前,“可这粟米,带着新鲜的稻谷味,显然是昨天刚装进去的。而且您看这粮袋,外面的麻绳还是新的,没有磨损的痕迹——真正运输的漕船,粮袋的麻绳早就磨得发亮了。”
周围的脚夫和漕丁们都看了过来,有人偷偷点头——他们都知道,漕船上的好粮都是临时换的,为的就是应付查验。
冯承业的额头渗出冷汗,强辩道:“老丈不懂漕运的规矩!这是新征收的漕粮,自然是新粮袋、新粟米!”
“哦?那咱们再看看其他船舱。”赵宸翊说着,走向漕船的后舱。冯承业想拦,却被周虎挡住了去路。
后舱的舱门紧锁着,冯承业的脸色更白了:“侯爷,后舱装的是漕运衙门的文书,没什么好看的……”
“文书?”赵宸翊冷笑一声,拔出腰间的尚方宝剑,一剑劈开了锁,“本侯倒要看看,是什么文书,需要锁得这么严实。”
舱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刺鼻的盐味扑面而来。后舱里根本没有什么文书,而是堆着满满的盐袋,雪白的私盐从袋口漏出来,在晨光里泛着光。
周围的人都惊呆了,脚夫们纷纷议论起来:“果然是私盐!我就说漕船怎么这么轻!”“冯总督竟然敢用漕船运私盐,胆子也太大了!”
冯承业慌了,上前一步想把舱门关上,却被赵宸翊拦住了。“冯总督,”赵宸翊的声音冰冷,“这就是你说的‘按律运输’?这就是你说的‘漕粮足额’?”
冯承业浑身发抖,却还想狡辩:“侯爷,这是误会!这私盐是盐商临时放在这里的,本督不知道……”
“不知道?”赵宸翊从盐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沈记盐铺,运往扬州”,还有冯承业的亲笔签名,“这上面的签名,也是误会吗?”
冯承业看到纸条,腿一软,差点跪倒在地。周围的漕运吏员们都慌了,有人想偷偷溜走,却被周虎的人拦住了。
“把冯承业拿下!”赵宸翊大喝一声,周虎和几个护卫立刻上前,把冯承业捆了起来。
“赵宸翊!你敢捆本督!”冯承业挣扎着,“本督是漕运总督,是二皇子的舅舅!你要是敢动我,二皇子不会放过你的!”
“二皇子?”赵宸翊冷笑,“本侯奉旨查漕,别说你是二皇子的舅舅,就算是二皇子本人,犯了法,本侯也照查不误!”
周围的百姓和脚夫们都欢呼起来——他们早就看不惯冯承业的贪腐了,如今看到他被拿下,都觉得解气。
赵宸翊转身对王河生说:“老丈,你带人查验其他漕船,把私盐的数量都记录下来。宋平,你带文书去漕运衙门,查封所有账册,不能让任何人销毁证据。林缚,你去苏州府衙,让张启配合咱们查案,要是他敢不配合,就一并拿下!”
众人领命而去,码头顿时忙碌起来。赵宸翊看着被捆起来的冯承业,眼神锐利——拿下冯承业,只是第一步,他还要找出沈万山和二皇子勾结的证据,把这伙贪腐分子一网打尽。
四、盐铺探秘,抓住关键人
拿下冯承业后,赵宸翊让周虎把他关在苏州府衙的大牢里,严加看管。随后,他带着林缚和几个护卫,去了沈万山的盐铺——江南最大的盐铺“沈记盐铺”。
沈记盐铺位于苏州最繁华的街道上,门面宽敞,里面摆满了盐罐,可柜台后的伙计却神色慌张,看到赵宸翊进来,连忙想去报信,却被周虎拦住了。
“沈万山在吗?”赵宸翊走到柜台前,声音平静。
伙计哆哆嗦嗦地说:“老……老东家不在铺子里,去……去扬州了。”
“去扬州了?”赵宸翊挑眉,“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昨天晚上。”伙计的声音更抖了。
赵宸翊心里清楚,沈万山肯定是听到了冯承业被拿下的消息,想逃跑。“林缚,你让人去查苏州到扬州的水路,看看沈万山坐的是哪艘船。”他说着,走向盐铺的后院。
后院的门也锁着,周虎一脚踹开了门。后院里堆着满满的盐袋,比前院的盐袋大了一倍,上面印着“漕运专用”的字样——这正是漕船上运的私盐。
“把这些私盐都查封了,”赵宸翊对身后的文书说,“记录下数量,作为证据。”
就在这时,盐铺的后门突然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穿着黑缎马褂的中年人想偷偷溜走,却被周虎抓了回来。“你是谁?”赵宸翊问道。
中年人浑身发抖,不敢说话。林缚上前一步,拿出一张画像——这是之前周虎暗中画的沈万山的管家王福的画像。“你是王福吧?沈万山的管家。”
王福脸色惨白,瘫倒在地:“大人饶命!小人只是个管家,什么都不知道……”
“不知道?”赵宸翊蹲下身,看着王福,“冯承业已经招了,说漕船上的私盐都是你安排的,分赃的账本也是你保管的。你要是老实交代,本侯可以饶你一命;要是敢撒谎,就别怪本侯不客气。”
王福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了,哭着说:“大人,小人招!小人全都招!私盐是沈万山让小人跟冯承业合作运的,每次运八十石私盐,沈万山分三成,冯承业分四成,剩下的三成给扬州知府柳文彦和其他漕官……分赃的账本,藏在盐铺后院的地窖里!”
赵宸翊眼睛一亮——账本就是最直接的铁证!“周虎,你带几个人,跟王福去地窖找账本。”他吩咐道,“林缚,你让人看住王福,别让他耍花样。”
周虎跟着王福去了地窖,没多久,就抱着一摞账本出来了。账本是用牛皮纸做的封面,上面写着“漕盐分赃明细”,里面记录着近三年来每次私盐运输的数量、金额和分赃比例,还有冯承业、柳文彦、沈万山等人的亲笔签名。
赵宸翊翻开账本,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气得手都在抖——三年来,他们通过漕船运私盐,一共赚了近千万两白银,而这些钱,都是从百姓和朝廷身上刮来的!
“把账本收好,”赵宸翊站起身,声音冰冷,“沈万山想逃去扬州,柳文彦肯定会接应他。周虎,你带护卫立刻去扬州,在漕道上设伏,一定要把沈万山抓回来。宋平,你整理账本和王福的供词,形成完整的卷宗,咱们随时准备上奏朝廷。”
周虎和宋平领命而去。赵宸翊看着盐铺里的私盐,又看了看远处忙碌的码头,心里暗暗发誓——他一定要把这些贪腐分子绳之以法,还江南漕运一个清明,还百姓一个公道。
四、扬州设伏,抓获沈万山
周虎带着十几个护卫,快马加鞭赶往扬州。按照王福的交代,沈万山坐的是一艘乌篷船,船上挂着“沈记盐铺”的灯笼,会沿漕道从苏州运往扬州,预计傍晚时分到达扬州码头。
周虎赶到扬州漕道的必经之地——瓜洲古渡时,太阳刚西斜。他让人在古渡旁的树林里埋伏起来,自己则换上一身渔夫的衣服,坐在河边钓鱼,观察过往的船只。
没过多久,一艘挂着“沈记盐铺”灯笼的乌篷船缓缓驶来。船上站着几个精壮的护卫,船头坐着一个穿着锦缎长衫的中年人,正是沈万山。
“就是他!”周虎压低声音,对身后的护卫说,“等船靠岸,咱们再动手,别惊了他。”
乌篷船慢慢靠岸,沈万山刚要下船,周虎突然站起身,大喊一声:“拿下!”
十几个护卫从树林里冲了出来,瞬间围住了乌篷船。沈万山的护卫想反抗,却根本不是周虎等人的对手,没一会儿就被制服了。
“你们是谁?敢拦本老爷的船!”沈万山又惊又怒,“本老爷是江南盐商总商,跟二皇子府有关系,你们要是敢动我,二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
“二皇子?”周虎冷笑一声,拿出尚方宝剑的剑穗,“我们是靖安侯的人,奉旨查漕。沈万山,你勾结冯承业,用漕船运私盐,中饱私囊,证据确凿,还敢狡辩!”
沈万山看到剑穗,脸色瞬间惨白——他知道,靖安侯赵宸翊是二皇子的死对头,这次被他抓住,肯定没好果子吃。“侯爷饶命!”沈万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小人只是一时糊涂,跟冯承业合作运私盐,求侯爷饶小人一命!小人愿意把所有赃款都交出来,只求侯爷别杀我!”
“饶你一命?”周虎一把揪住沈万山的衣领,“你用漕船运私盐,导致漕粮短缺,百姓吃不上饭,军粮掺霉米,你觉得你该饶吗?”
沈万山吓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周虎让人把沈万山捆起来,押上马车,又让人搜查乌篷船——船上除了沈万山的行李,还有一箱满满的银票,足足有五十万两,都是这次运私盐赚的赃款。
“把银票收好,”周虎对身边的护卫说,“这都是证据,不能丢了。咱们现在就回苏州,向殿下复命。”
与此同时,在苏州府衙里,宋平正在整理卷宗。他把王福的供词、分赃账本、私盐的数量记录,还有冯承业的认罪书,一一整理成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林缚则在查漕运衙门的旧账,发现近三年来,江南漕运的“损耗率”高达三成,比正常损耗率高出十倍,而且这些“损耗”的漕粮,都没有销毁记录——显然是被换成私盐了。
赵宸翊看着整理好的卷宗,心里松了一口气。现在,冯承业被抓,沈万山被擒,账本和供词都有了,江南漕运贪腐的铁证已经确凿,接下来,就是上奏朝廷,严惩这些贪腐分子了。
五、上奏朝廷,严惩贪腐
三日后,赵宸翊带着完整的卷宗,和被押解的冯承业、沈万山等人,回到了长安。章和帝在太极殿召见了他,看到卷宗里的记录和证据,气得拍了御案。
“冯承业、沈万山,你们好大的胆子!”章和帝看着跪在殿下的冯承业和沈万山,声音冰冷,“竟敢勾结起来,用漕船运私盐,中饱私囊,连军粮都敢掺霉米!你们可知,这是诛九族的大罪!”
冯承业和沈万山吓得魂飞魄散,连连磕头:“陛下饶命!臣(小人)一时糊涂,求陛下饶命!”
“饶命?”章和帝冷笑,“你们贪污的近千万两白银,是百姓的血汗钱,是朝廷的军饷!你们害百姓吃不饱饭,害士兵吃霉米,这笔账,怎么算?”
赵宸翊上前一步,躬身道:“陛下,冯承业、沈万山等人罪大恶极,按律当斩。扬州知府柳文彦参与分赃,也应一并严惩。另外,江南漕运的制度也需要改革,臣建议设立漕运巡查署,由朝廷直接派官巡查,避免再出现贪腐现象;同时,提高漕丁的俸禄,严禁漕官克扣,确保漕粮足额运输。”
章和帝点了点头:“赵宸翊说得对!冯承业、沈万山、柳文彦等人,判斩立决,家产抄没,用于填补漕粮亏空;漕运巡查署,就由你负责组建,选派正直可靠的官员去江南巡查。另外,你在江南查漕的功绩,朕记在心里,赏你黄金百两,绸缎千匹。”
“谢陛下。”赵宸翊躬身谢恩。
随后,章和帝下旨,将冯承业、沈万山、柳文彦等人押赴刑场,斩立决。消息传到江南,百姓们纷纷拍手称快,有的还自发地在街头放鞭炮——他们终于不用再受贪腐漕官的压榨了。
漕运巡查署组建后,赵宸翊选派了幕僚馆里正直可靠的官员去江南,林缚也被派去担任漕运巡查署的副署长,负责整理漕运的账册和制度。在他们的努力下,江南漕运的制度逐渐完善,漕粮的运输也恢复了正常,漕丁们的俸禄足额发放,再也没有人敢用漕船运私盐了。
这日,赵宸翊收到林缚从江南寄来的书信,信里说江南的漕粮已经足额运往京城,漕丁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百姓们也纷纷称赞朝廷的新政。赵宸翊看着书信,心里满是欣慰——他知道,这次江南查漕,虽然历经艰险,但终究没有辜负陛下的信任,没有辜负百姓的期望。
可他也知道,二皇子赵宸渊因为冯承业等人的死,肯定会更加恨他,接下来的日子,还会有更多的挑战等着他。但赵宸翊并不害怕——他有幕僚馆的伙伴,有百姓的支持,还有陛下的信任,只要他坚持为百姓做事,就一定能克服所有的困难,让大雍的江山更加稳固。
六、尾声:漕运新声
半年后,江南漕运彻底恢复了清明。漕船上的漕粮不再掺沙,漕丁们的俸禄足额发放,码头边的脚夫和百姓们脸上都露出了笑容。赵宸翊再次来到江南,看到满载漕粮的漕船驶向京城,心里满是感慨。
林缚陪着他站在苏州码头上,指着远处的漕船:“殿下,您看,这是本月运往京城的漕船,一共一百艘,每艘都足额装载,没有掺一粒沙、一粒霉米。漕丁们都说,这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运这么‘干净’的漕粮。”
赵宸翊点了点头,目光落在码头边的一块石碑上——那是百姓们自发立的石碑,上面写着“靖安侯查漕,还我清明”八个大字。“这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他说,“要是没有幕僚馆的伙伴,没有百姓的支持,咱们也做不到这些。”
王河生和宋平也来了,他们刚从黄河堤岸考察回来。“殿下,黄河的堤岸维护得很好,”王河生笑着说,“今年汛期,肯定不会再决堤了。而且咱们在江南推广的西域粟种,也长得很好,预计秋收时,能多收三成粮。”
宋平也道:“律法署在江南也设立了分署,解决了不少民间纠纷。百姓们都说,现在的江南,不仅漕运清明,律法也公正了,日子越来越好过了。”
赵宸翊看着身边的伙伴,又看了看远处繁忙的码头,心里满是希望。他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有很多事要做——关中的农桑要继续推广,黄河的水利要继续维护,江南的漕运要继续巩固,二皇子的阴谋要继续防备。但他相信,只要他们一直坚持为百姓做事,就一定能让大雍的江山越来越繁荣,让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幸福。
夕阳下,苏州码头的漕船扬起风帆,驶向远方。漕丁们唱起了欢快的漕运号子,声音洪亮,回荡在大运河上空——这是江南查漕之后,漕运响起的新声,也是大雍王朝走向清明的希望之声。而赵宸翊知道,他的使命,还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