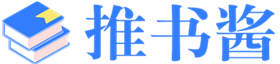如果你喜欢历史脑洞类型的小说,那么《逆天命:元清明》绝对值得一读。小说中精彩的情节、鲜活的角色以及深入人心的故事,都会让你沉浸其中,难以自拔。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最新章节为第12章,总字数已达124308字,喜欢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主要讲述了: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七,黄河在曹州白茅堤溃决的前夜,郓城县的老河工陈石匠正蹲在堤岸下修补裂缝。他手里的夯锤浸了二十年黄河水,木柄上的裂纹里嵌着泥垢,像条凝固的河。“爹,歇会儿吧,县太爷都走了,谁还管这破堤…

《逆天命:元清明》精彩章节试读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七,黄河在曹州白茅堤溃决的前夜,郓城县的老河工陈石匠正蹲在堤岸下修补裂缝。他手里的夯锤浸了二十年黄河水,木柄上的裂纹里嵌着泥垢,像条凝固的河。“爹,歇会儿吧,县太爷都走了,谁还管这破堤?”儿子陈栓柱递过来个粗瓷碗,碗里是掺了野菜的糊糊。
陈栓柱的指尖在碗沿捏出红痕。方才递碗时,他看见爹的手背被夯锤震出了血泡,血珠渗进黏土里,和黄河的泥沙混在一起。他总觉得爹太傻——监工把石料换成沙土的事,全县的河工都知道,可只有爹还在拼命修补裂缝。方才监工喊“用沙土填堤”时,他攥紧了拳头,指甲几乎嵌进掌心:这些人分明是把黄河当成了能随意糊弄的账册,而他们这些河工,就是要被填进裂缝的沙土。
陈石匠没接碗,把最后一捧黏土砸进裂缝:“县太爷走了,黄河不走。”他抬头看天,乌云压得很低,河风裹着水汽打在脸上,“这雨再下三天,别说裂缝,整段堤都得塌。”
堤岸上的监工突然扯着嗓子喊:“都别干了!府里来令,石料改运密宗寺院,以后用沙土填堤!”陈石匠手里的夯锤“当啷”掉在地上——他上个月就听说,监工把修堤的石料换成沙土倒卖,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爹,咱也走吧。”陈栓柱拉着他往回走,掌心的汗把爹的袖口洇湿了一片,“留在这里,要是堤塌了,监工肯定把咱推出去顶罪。”他想起三天前,邻村的李河工因为抱怨了句“沙土挡不住水”,就被监工打断了腿,扔在堤岸下喂狼。他不想爹也落得那样的下场——哪怕要逃去当流民,至少能活着。
陈石匠看着堆在堤角的沙土,颗粒粗得能看见石砾——这东西堵老鼠洞都嫌松,怎么能堵黄河?
回到家时,妻子正把最后一袋粮食塞进炕洞。土坯房的墙缝里渗着水,锅里的观音土糊糊冒着热气。“刚才有河南来的逃荒的说,黄泛区那边已经有人吃小孩了。”妻子的声音发颤,“咱要不也逃吧?去江南投奔你表弟。”
“往哪逃?”陈石匠蹲在灶门前,火柴在手里划了三次才点燃,“黄河真决口,方圆百里都是水;不决口,监工迟早要把咱这些河工卖去密宗寺院当祭品。”他想起上个月,邻村的王木匠就是被监工以“怠工”为由抓走的,后来有人在寺院的墙角看见他的骨头。
陈栓柱蹲在门槛上,看着母亲把观音土拍成饼。土腥味钻进鼻子时,他突然想起去年麦收,爹偷偷藏了把新麦,磨成粉给娘做了碗面条——那香味现在想起来,还能让喉咙发紧。他摸了摸藏在怀里的半块麦饼,是前天偷偷从监工的剩饭里捡的,本来想等爹生日时拿出来,现在却觉得,或许等不到那天了。
三更时,雨突然大了。陈石匠披着蓑衣站在院里,听见黄河的咆哮声比往常更凶,像有无数头野兽在下游冲撞。他摸出藏在床底的羊皮筏子——那是他用三年前修堤时偷偷留下的木料做的,本想等儿子娶媳妇时当嫁妆,现在倒成了救命的东西。
“栓柱,把你娘扶到筏子上。”他把粮食和水袋捆在筏子上,“要是水来了,就往东南走,那边地势高。记住,别回头,别捡浮在水上的东西——那都是死人的物件。”
陈栓柱的手指在筏子的木框上抠出几道印子。这筏子他帮着爹削过木片,缝过羊皮,当时爹说:“等你娶了媳妇,就用这筏子载着她去逛庙会。”现在筏子要载着他们逃荒,他突然觉得眼睛发酸——那些关于庙会、新媳妇、麦饼的念想,好像被雨泡得发了霉。
天快亮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像天塌了。陈栓柱冲出屋,看见西北方向的水天连成一片,浑浊的水头正往这边涌,田埂上的野草被水头压得贴在地上,逃难的人在水里挣扎,像被冲散的蚂蚁。
“快上筏子!”爹把娘推上筏子,又把他拽过来,“抓紧了!”羊皮筏子刚离岸,水头就到了——陈栓柱看见邻居家的土坯房像纸糊的一样塌了,房梁上还挂着他家闺女的红头绳;监工的马棚被卷进水里,马嘶声瞬间被水声吞没。他死死攥着筏子的绳子,指节发白——那马棚的柱子,还是他去年帮着立的。
筏子在浪里颠得厉害,陈栓柱看见水里漂着粮食袋(大概是从官仓冲出来的)、女人的绣花鞋、孩子的虎头帽。有个抱着门板的老汉朝他们喊:“往南!往南有高地!”话音刚落,就被个漂浮的树干撞翻,再也没露头。他赶紧低下头,不敢再看——那老汉昨天还给他递过旱烟,烟杆上刻着“平安”两个字。
母亲突然指着前面哭:“是张寡妇!”陈栓柱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张寡妇抱着根椽子,怀里还搂着个孩子——那孩子是她去年从黄泛区捡的,一直当亲生的养。前几天他还看见这孩子在堤岸上追蝴蝶,手里攥着朵野菊花。“抓稳筏子!”爹用篙杆勾住椽子,他赶紧把她们拉上来。
“我男人……我男人还在堤上……”张寡妇抱着孩子发抖,她男人是堤上的民夫,昨天还来借过盐。陈栓柱摸了摸怀里的麦饼,突然想把它给那孩子——可他又怕,这是家里最后一点能吃的粮食了。
筏子漂到正午时,雨小了些。水面上开始浮着尸体,有穿着官服的(大概是来不及逃的县吏),有戴镣铐的(应该是牢里的囚犯),还有些孩子的尸体,小手还保持着抓东西的姿势。陈栓柱突然干呕起来,胃里的酸水烧得喉咙疼——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爹带他在黄河边捞鱼,那时的河水是清的,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
爹扇了他一耳光:“别吐!省点力气!”
他咬着牙把酸水咽下去,舌尖尝到点血腥味。他知道爹不是狠心——在水里,力气比眼泪金贵。
他们在一片杨树林里靠岸时,已经漂了三十里。树林里挤满了逃难的人,有人在树上搭窝棚,有人在烧浮木取暖,还有个老婆婆抱着个死孩子,用碎布给孩子擦脸,嘴里念叨着:“咱不玩水了,咱回家……”陈栓柱赶紧转过头,却看见那孩子的脚上,穿着双和他去年穿坏的那双一模一样的布鞋。
陈石匠刚把羊皮筏子拖上岸,就看见个穿绿袍的官差在打人。“都给我站起来!县太爷有令,青壮年去修临时堤坝,妇女儿童去运沙土!”官差的鞭子抽在一个老汉身上,“谁要是敢躲,直接扔回水里喂鱼!”
“修堤?用啥修?”爹走过去,陈栓柱看见官差身后堆着些烂草和树枝——这东西连小溪都堵不住,更别说黄河。他突然想起那些被倒卖的石料,现在大概正铺在密宗寺院的台阶上,被僧侣们踩在脚下。
官差瞪着爹:“少废话!朝廷马上就派赈灾粮来了,现在不修堤,你们喝西北风?”
“赈灾粮?”张寡妇突然笑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去年俺男人修堤时,就听你们说有赈灾粮,结果粮被运去寺院喂狗,他还被石头砸断了腿!”她怀里的孩子被吓哭,哭声在树林里飘得很远。
官差的鞭子朝张寡妇抽过来,被爹用篙杆挡住。“你敢抗命?”官差喊来两个兵丁,“把这老东西拖去沉水!”兵丁刚要动手,树林里突然响起喊声:“别碰他!”
十几个民夫拿着铁锹和木棍走过来,为首的是个瘸腿的汉子——陈栓柱认得,他是去年修堤时被砸断腿的王二愣。“要修堤可以,”王二愣拄着铁锹,“先让县太爷把贪污的修堤款拿出来,把监工换的沙土换成石料!不然,谁也别想动!”
陈栓柱的手心又开始冒汗。他怕兵丁拔刀,怕官差喊人,可看着围过来的民夫,看着他们眼里的火,他突然觉得,就算兵丁拔刀,他们也不会退——就像黄河决口,挡是挡不住的。
官差看着围过来的民夫,脸色发白:“你们……你们想反?”
“反?”王二愣笑了,“我们只想活命!”他指向远处的水头,“黄河决口,不是因为我们没修堤,是因为你们把石料卖了,把粮食贪了!现在还想让我们用命填河?”
民夫们的喊声越来越大,兵丁吓得往后退。官差突然往回跑,边跑边喊:“你们等着!我这就去报官,让密宗国师来收了你们这些邪魔!”
看着官差的背影,陈栓柱突然觉得,这水头冲垮的不只是县城,还有他们对朝廷最后一点指望。以前他总觉得,只要听话,就能活下去;可现在他才明白,有些时候,听话就是等死。
王二愣走过来,拍了拍爹的肩膀:“老哥,别信官差的。密宗的人来,只会把咱们当祭品,不会管咱们死活。”
他指着树林深处:“那边有个破庙,咱们去那里聚着,自己修筏子,自己找吃的。等水退了,就去黄泛区——听说那边有个‘渠帅’,带着流民自己过日子,不用看官府脸色。”
陈栓柱摸了摸怀里的麦饼,饼已经被体温焐软了。他突然想,要是真有这样的地方,是不是能让那孩子吃上口热的?是不是能让娘不再吃观音土?
“我跟你们去。”爹把筏子上的粮食卸下来,“但咱不能只逃。”他捡起块木板,用炭在上面写:“要活命,先夺粮”——这是他年轻时听老河工说的,当年元军刚占中原时,有个河工就是靠这六个字,带着百姓守住了堤。
陈栓柱看着木板上的字,突然觉得比官府的告示还实在。告示上写着“赈灾”“安民”,可木板上的字,写的是能摸到的粮食,是能活下去的路。
跟着王二愣往官仓走时,水已经退了些,露出的泥地里陷着尸体和杂物。有个民夫突然停下,从泥里挖出个布包,打开一看,是件小孩的棉袄,上面绣着朵桃花——他的手开始发抖,陈栓柱知道,这是他没来得及带走的孩子的衣裳。他赶紧掏出怀里的麦饼,塞给那民夫:“吃点吧,有力气才能走。”民夫看着他,突然捂住脸哭了——那哭声比水头的咆哮还让人难受。
官仓在县城的高地上,院墙被水头冲塌了一半。王二愣让民夫们躲在断墙后,自己先摸过去——陈栓柱看见两个兵丁正往麻袋里装粮食,麻袋上印着“赈灾粮”三个字,可他们装的却是糙米,比平时给民夫吃的谷糠好十倍。他突然想起爹说的“官仓的老鼠都比民夫吃得好”,以前不信,现在信了。
“动手!”王二愣喊了一声,陈栓柱跟着冲进去。兵丁想拔刀,被爹一篙杆打翻。他看着缩在墙角的兵丁,他们的衣服比自己的还破,鞋底子都磨穿了。“别杀他们。”爹说,“他们也是被官差逼的。”他打开粮仓的门,里面堆着十几麻袋粮食,还有些布匹和药材——这大概是县太爷没来得及转移的私产。陈栓柱突然觉得,这些粮食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心里发慌。
“快搬!”王二愣指挥着,“留两袋给兵丁,让他们自己找活路。”陈栓柱扛着半袋糙米往回走,粮食压得肩膀疼,心里却松快——这是他第一次不是靠乞讨、不是靠施舍,而是靠自己拿回来的粮食。
回到破庙时,张嫂子已经生起了火,孩子们围着火堆烤衣服。爹把药材分给受伤的人,看着王二愣给民夫们分粮——每人两升糙米,不多,但够吃三天。“三天后,水应该能退得差不多了。”王二愣说,“咱们往东南走,去黄泛区找渠帅。听说他那里有粮,还教百姓修堤,不用看官府脸色。”
陈栓柱把分到的糙米倒进母亲的布包里,米粒滚出来时,他看见有颗糙米上还带着点泥土——这是真正长在地里的粮食,不是官仓里冷冰冰的数字。他突然想,要是能一直这样,靠自己的力气换粮食,靠自己的手艺修堤,就算住在草棚里,也比现在强。
他突然指着庙外:“爹,你看!”远处的水天相接处,有个黑点在移动——越来越近,才看清是艘小船,船上插着面红旗,旗上绣着个“石”字。
“是渠帅的人!”有个从黄泛区逃来的民夫喊,“他们来救人了!”小船靠岸后,跳下几个带刀的汉子,为首的举着面红巾:“我们是红巾军!奉渠帅令来救灾民——有吃的吗?有地方住吗?”
陈栓柱看着那面红巾,在夕阳下像团火。他想起刚才抢粮时的勇气,想起那两个兵丁的破鞋,突然觉得,这红巾或许不是官差说的“邪魔”,是能让他们活下去的人。
王二愣把红巾军的人领进庙,看着他们带来的草药和干粮,突然红了眼:“你们……你们真的是来救人的?”红巾军的首领笑了,从怀里掏出个饼子,递给张嫂子怀里的孩子:“不仅救人,还要让大家有饭吃,有堤修——用真石料修的堤。”
陈栓柱看着孩子啃饼子的样子,饼渣掉在衣襟上,孩子赶紧捡起来塞进嘴里。他突然觉得,这才是粮食该有的样子——不是被藏在官仓里发霉,不是被倒卖给盐商,是填进饿肚子的人嘴里,是让孩子能笑出声。
红巾军的首领叫赵勇,是汝宁卫逃出来的士兵——陈栓柱听说过汝宁卫的事,知道他们是被李千总逼反的。“我们渠帅说了,黄河决口不是天谴,是官逼民反。”赵勇给民夫们讲红巾军的规矩,“谁修堤给谁粮,谁种粮谁得粮,不分汉人和胡人,只要肯干活,就有活路。”
陈栓柱摸了摸自己的手——这双手能搬石料,能修筏子,能种庄稼。要是真有这样的地方,他或许能让爹娘过上好日子,不用再吃观音土,不用再怕监工的鞭子。
第二天一早,红巾军的船带着第一批灾民往黄泛区走。爹留在破庙,帮赵勇接应后面的人。陈栓柱看着水头冲垮的县城,突然觉得,垮了也好——旧的堤塌了,才能修新的;旧的世道烂了,才能有新的。
有个红巾军的士兵正在给断墙刷红漆,刷成一道红线。“这是啥?”他问。士兵笑了:“是界碑——红线里是咱们红巾军的地盘,以后这里的堤,咱们自己修;这里的粮,咱们自己种;这里的人,再也不用怕水头,不用怕官差,不用怕密宗的祭品。”
陈栓柱蹲下来,用手指在未干的红漆上画了个简单的筏子——他想告诉后来的人,这里有人靠这个活了下来,也有人靠这个去了能活命的地方。红漆在雨里慢慢渗进墙里,像血,也像新生的芽。他突然觉得,这道红线比官府的城墙还结实——城墙挡不住黄河,可这红线能拦住人心的溃散。
远处传来黄河的咆哮,不再像野兽,倒像在给离开的人送行。陈栓柱知道,这水头冲垮了三座县城,却冲不散想活命的人——他们会像黄河的泥沙一样,在新的地方沉淀下来,长出新的庄稼,修起新的堤坝。
小说《逆天命:元清明》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