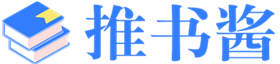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柳三行述》是一本引人入胜的年代小说,作者“有人乎”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本书的主角虎妹牛哥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最新章节第14章,热爱阅读的你千万不要错过这场精彩的阅读盛宴!主要讲述了:六七十年代的书荒像层薄纱,看着朦胧,却挡不住我扒着字缝儿找故事的劲头。那会儿能摸到的书金贵得很,谁家要是有本没封面的旧书,能在周围里传着看好久,最后变成手抄本。我家算是条件稍好的,母亲在资料馆工作,总…

《柳三行述》精彩章节试读
六七十年代的书荒像层薄纱,看着朦胧,却挡不住我扒着字缝儿找故事的劲头。那会儿能摸到的书金贵得很,谁家要是有本没封面的旧书,能在周围里传着看好久,最后变成手抄本。我家算是条件稍好的,母亲在资料馆工作,总能从废纸堆里捡回些”漏网之鱼”,《渔岛怒涛》里的海岛枪声、《红岩》牢房里的绣红旗,还有《高玉宝》里那句”我要读书”“半夜鸡叫”,都比过年的饺子还让人惦记。书架上最扎眼的是浩然的书,《艳阳天》《金光大道》翻得书脊发白,字里行间的庄稼地和社员们,比隔壁邻居的叔叔大爷还熟。老舍的京味儿、高尔基的《童年》、保尔的钢铁意志,再加上通读的毛选和各种巴掌大的小册子,小人书,就这么杂七杂八喂大了我的少年时代。
记得有次在妈妈悄悄带回一本缺页的《欧阳海之歌》,回家连夜看的入迷。母亲说太晚了关灯睡觉,大人明天还要上班。我就钻到被子里打着手电筒看。看到欧阳海拦惊马的那瞬间我脑子里全是想象的样子,内心深处佩服欧阳海的勇敢,想着那高大的马,想着他是怎么用身体拦下惊马,做梦都是插图里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那时候哪儿懂什么叫”精神食粮”,只知道这些方块字能带我去好多地方,见好多不一样的人,比家门口那条走了八百遍的路要有意思多了。
中学的政治老师刁家屯,是个穿一身洗得发白中山装的瘦高个儿,圆脸鼻梁上架着副断了腿用胶布粘好的眼镜。
他讲课特别投入,讲到激动处就像终于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大秘密那样,声音变快而急切,他用粉笔写板书时很用力,粉笔灰像雪花似的落下来,他也不在意。”世界是物质的”我回家跟父亲说老师这么说的。父亲说,对啊,不仅是物质的,还是运动的,还是有规律的!我就觉着这句话挺有意思,但是从来没把这句话与哲学拉上关系。
那会儿我是班里的政治课代表,总帮老师抱作业本,同时会写一些读书后的感想当日记交给老师。
他常跟我们班主任夸我,班主任家访也常常看到我在那里看书写字。有次老师说:”小柳啊,多看书很好,但是,读书是间接经验,我给你讲课也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们,也是间接经验,你还要去走向社会参加实践,只有亲自接触到感受到的,才是直接经验。毛主席说,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也就是通过实践发现问题,再回来带着问题学,学明白了,再到实践中证明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明白了道理,实践出真知。”我似懂非懂地点头,后来,我又反复读了《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随着时间的发酵,我感觉这些小册子里的东西慢慢融入了我的认知中,渐渐的我可以顺着指导发现身边问题的规律,可以防微杜渐,这都是后话了。
某天放学,我在走廊撞见隔壁班的女生见了我主动打招呼,像是同班老同学跟我聊学习。毕业后她也总通过与她住在同一个胡同里的,我的同班同学帮忙与我联系来往,我那会儿不明白其中原因,只当是同学间的无意巧合,聊几句就各走各的。
有一次她跟我在一起聊她的家,她的家事儿,她的纠结,就像想跟我诉说出她的一切,希望我给个答案一样,聊了很久。我很茫然,不知道她为什么说了那么多,我默默听着,我不曾记得我们是怎么结束的聊天,更记不得我说了什么,只记得从此我们就是关系挺好的同学了。
直到四十多年后的年级聚会上,鬓角都白了的我们坐在茶馆里,她忽然指着我笑:”你还记得不?初中时我总跟着你,你还躲我呢。”我端着茶杯的手顿了顿,确实有这么回事,可我一直没明白缘由。她噗嗤笑了,眼角的皱纹堆成朵花:”你忘啦?刁家屯老师啊!他在班会上念你那篇《我的同学孟兰》,说这同学世界观正,看问题透,将来一定错不了。我这不就好奇嘛,四处打听才找机会巧遇你,就想跟你认识。”
我这才想起那篇作文。孟兰是班里一个圆圆娃娃脸的女生,她是特别内向,开口就脸红的女生,偏偏每天愿意绕远来我家院招呼我一起走,每当听到她文文弱弱推开大院门,喊我一声“柳三!”我都会扯着嗓子答应一声“来啦!”。
因为我从小牙有问题,每次牙疼半个脸都肿起来老大,有一次又牙疼了,孟兰就带着韭菜籽,在我家用香油炸了,再用小碗扣住,接着她找了一张纸,中间捅一个洞,然后把熏好的碗扣在我耳朵上,说能把牙虫子吸走。孟兰的贴心让我感动,所以写了作文也是感谢表扬孟兰对我的帮助。
刁老师给我批了个”优”,还在后面画了个大大的感叹号。没想到这篇作文竟成了介绍信,让我与隔壁班的同学的名字在彼此的通讯录里躺了几十年,从BP机到座机,再到智能手机,隔三差五就得唠几句近况。去年她孙子满月,还特意快递来一包红鸡蛋,说:”当年刁老师没说错,你这人就是靠谱。”我捧着那包鸡蛋笑了半天。
可那会儿的我,连”世界观”三个字是怎么回事儿都还没弄清楚,更别说啥三观、方法论了。政治课本里”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我总当绕口令背,心想这就是科学总结出的道理——桌子是木头做的,河水会流动,太阳东升西落,这个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怎么又叫哲学?为什么叫哲学还是云里雾里,毕竟那时没有网,没有可以找答案的渠道,所有的问题,都要通过唯一通道,老师,至于书,遇见了能解惑,一旦一辈子没遇到有这样的书,那就永远无法解惑,所以,从我爸妈到我,我们都嗜书如命,只要有条件见到感兴趣的书就买下来,正所谓我们笃定: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道理。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等。如今,想知道什么领域的知识,网上都能找到,纸质书又占空间,又占家里的一些银两,真要看时纸变黄了,字感觉小了,内容也不一定与当下接轨了,就像儿子说我,现在买书就是一种情怀一种习惯,把书当奢饰品买了。
话说我读书认真,做事认真,却不会拐弯,更对人情世故感觉迟钝。
就像亲戚饭桌上的那次”岳父相”事件,能让我钻半年牛角尖。
那年过年在二姑家吃饭,表哥指着电视里的相声演员说:”这小子一看就是岳父相。”我嘴里的饺子差点喷出来,追着表哥问:”你认识他岳父?长得像吗?”一桌子人都笑了,二姑笑得直拍大腿,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我还不服气,梗着脖子说:”他没见到过人家的岳父岳父,那为什么说他是他岳父的长相?”
这事儿就像根小刺扎在我心里,过了小半年,又见到表哥,我逮着机会又问:”上次那演员,你到底见没见过他岳父?”表哥嘴里的酒差点呛出来,指着我对满桌人说:”你们看,她还记着呢!”七姑八姨们笑得前仰后合,三姨母揉着我的头发说:”傻闺女,说他是岳父相,不是说他像他岳父,是说他这模样、这性子,将来肯定是生闺女的命,等他闺女嫁了人,他不就是岳父了吗?”
我这才恍然大悟,乖乖,合着话还能这么说?绕了十八个弯儿!亲戚们从此认定我不会脑筋急转弯,做事一根筋,说我”纯”得像没开封的罐头。有次表妹找对象,三姨母偷偷跟我说:”你可别跟人家见面时瞎接话,别问人家’你妈是你亲妈不’这种傻话。”我摸着后脑勺笑,心里却有点委屈——我就是想不明白,话为啥不能好好说?非得绕来绕去的。
其实何止这些,七姑八姨的称谓我至今记不全。每次家庭聚会,母亲总得提前给我打预防针:”那个戴金镯子的是你表舅妈,穿蓝布衫的是你三姥姥,记不住就笑,别瞎叫。”可我偏不,非得凑过去问:”您是我妈的表姐还是表妹?”弄得人家哭笑不得。母亲总叹气:”这孩子,在人情世故上,成熟得比别人晚半拍。”
耳顺之年再琢磨,刁老师当年咋就看出我”世界观正确”了?我那会儿连世界观是啥都不知道,分明是六十岁后才慢慢咂摸出点味儿来——大概是我看的那些书,那些字里行间的英雄和好人,不知不觉在我心里有了烙印,让我觉得人就该像欧阳海那样勇敢,像草原英雄小姐妹那样执着,像红岩里的烈士那样有骨气。现在想老师说我的世界观就是烙印在我身上的这些精神吧?
要说最傻的一次,八十年代末,我家拆迁需要单位给个无房证明。这本是顺理成章的,经层层相关部门都过了,最后需要到一位位高权重的领导那里最后签字了。
我硬着头皮敲开他办公室的门,一进门就瞅见他办公室墙上挂着几幅工笔仕女图。我家是书画世家,从小在墨香里泡大,忍不住脱口夸道:”哎呦,这画是您画的?这线条,这设色,真见功夫!”
领导闻言抬起头笑了,一脸温和的谦虚道:”瞎画的,打发午休时间。”正说着,他的助手小李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个文件夹,看到我在,他眼睛一亮就冲画走过去:”陈局,我想求您一幅墨宝,这次可得给我留一幅!”
领导笑着看我一眼说:”小柳我还没给呢,哪儿轮得到你?”我听了心里那叫一个美,觉得领导看重我,连他助手都得往后排。那小李也太不懂事了,咋好意思随便要领导的东西呢?
我还高兴的说,能得一幅您的画我太高兴啦!听了我的话,那天领导的签字出奇地顺利,还笑着说:”小柳啊,以后家里有啥困难,直接来找我。”我揣着签好的单子,脚步轻快地走出办公室,觉得这领导真是体恤下属,比后勤那帮踢皮球的强多了。
现在想,那天领导可能会以为我已经承诺了,改天就会去找他买画吧,可惜我真的不是故意没听懂。这个顿悟,还是拜我都成了没人管的”天老大我老二”的年纪,在一次画展上,有朋友向我介绍用艺术品送礼的潜规则,那些套路,让我忽然像被雷劈了似的——迟到的顿悟啊!
当年领导哪里是看重我,分明是在变相提醒我呢!那小李更是在递话:想办事?得表示表示,买领导一幅画不就结了?答谢领导不显山不露水,既体面又隐蔽。领导的仕女图,说白了就是”价签”,我还傻呵呵地夸画好,难怪领导笑得那么意味深长。
合着我当年还傻呵呵等着领导”对我好”,难怪后来升职总在最后一步被人抢了先。有次单位评先进,民主投票我排第一,可最后公示名单里却没我的名。我去找领导问,领导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柳啊,你业务能力强,但还得注意与同事的关系。”我当时琢磨了半天,同事关系是啥?是得多帮同事打水扫地吗?现在才明白,人家是说我不懂”规矩”。
现在想想都后怕,在职四十年能有惊无险混过来,八成是靠老天爷赏饭吃,外加一身不知天高地厚的憨胆。有次跟当年的老同事聊天,她才告诉我:”你当年在会上直接提领导报表里的错,我们都替你捏把汗。”我这才想起有这么回事,当时只觉得错了就得指出来,哪想过别的。老同事叹着气说:”你呀,就是书读得太死,不懂水至清则无鱼。”
顿悟那天,我立马把网名改成”成熟的有点晚”。后来越想越觉得,哪是”有点晚”啊,简直是晚得一塌糊涂。
不过话说回来,傻人有傻福,至少活到现在,我还没因为执念那些弯弯绕绕把头发想白了,倒也落得个心里透亮。前阵子整理旧物,还有那本缺页的《欧阳海之歌》,忽然就明白了——当年刁老师说的”世界观”,或许不是书本里的大道理,而是心里的那点亮堂劲儿,是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
至于那些绕来绕去的话,那些藏在话后面的意思,我现在还是常常反应不过来。
是啊,开窍晚就晚吧,至少我这一辈子,没丢了那些书里教我的道理,没忘了那些字里行间的光。
小说《柳三行述》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