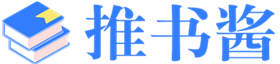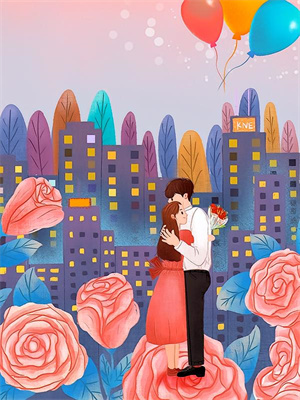简介
喜欢都市日常小说的你,有没有读过这本《山风拂讲坛》?作者“翕道”以独特的文笔塑造了一个鲜活的林砚形象。本书目前连载,赶快加入书架吧!
山风拂讲坛小说章节免费试读
中心校的二楼走廊总飘着股挥不散的味道——是粉笔灰混着旧纸张的干涩,又掺了点楼下食堂飘上来的菜籽油香,像把好几段不相干的日子揉在了一起。林砚踩着走廊里斑驳的绿漆地板往前走,每一步都能听见鞋底蹭过裂纹的细碎声响,和望溪教学点那片踩上去会发软的黄土地完全不同。
财务室在走廊尽头,两扇掉了漆的木门虚掩着,门楣上钉着的“财务室”木牌歪了半寸,边缘被摩挲得发亮。他推开门时,铰链发出“吱呀”一声闷响,像是谁在暗处轻轻叹了口气。屋里比走廊亮些,却也闷,阳光透过蒙着灰尘的玻璃窗斜射进来,在地面投下长条形的光斑,光斑里浮动的尘埃看得人发怔。
两张深棕色的旧办公桌对放着,桌面边缘的漆皮卷着边,像是被无数次手肘磨过。靠窗的那张摆着摊开的账本,红黑两色的笔迹密密麻麻挤在格子里,旁边堆着半盒回形针,还有个掉了瓷的搪瓷杯,杯沿沾着圈褐色的茶渍。另一张是空的,桌面隐约留着方形的印痕,该是之前摆过东西,如今只剩几道浅浅的划痕,像谁没说完的话。窗台上摆着盆蔫蔫的绿萝,叶子边缘卷着黄边,花盆是个旧奶粉罐,罐身还印着半块模糊的卡通小熊。
“进来吧,以后这张就是你的工位。”靠窗的女人抬头,声音温温的,带着点刚从账本里抬眼的倦意。林砚看见她指尖沾着块淡蓝色墨水渍,像是不小心蹭上去的,衬得那截手指格外白。女人起身时,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划开一道刺耳的声响,她从抽屉里翻出本深蓝色封皮的书递过来,封面上“财务制度”四个烫金大字磨得发暗,书脊处用透明胶带粘过,胶带边缘已经泛黄。
“这是咱们的‘护身符’,”女人笑了笑,用指甲蹭了蹭指尖的墨水渍,顺手往账本里夹了张皱巴巴的请假条,“我叫苏敏,去年来的财务室。昨天算食堂账到半夜,低年级的加餐费算错了三块二,差点被家长堵在门口,全靠这书里的条款帮我说清的——这已经是它救我的第三次了。”
林砚接过书,指尖触到书页边缘的褶皱,硬邦邦的,像是被人反复翻过无数次,连扉页都磨出了毛边。他把书放在空桌上,转身去拎脚边的背包,背包带已经被磨得发亮,是在望溪时天天背着重教案走山路磨的。拉开拉链时,一本蓝色封皮的教案露了出来,边角都卷了,像是被反复塞进抽出过很多次。
这是他在望溪教学点带三年级语文时用的。封面是他自己用蓝漆刷的,如今漆皮掉了些,露出底下的牛皮纸。扉页贴着张彩色粉笔涂的小太阳,红橙黄三色叠在一起,边缘涂得歪歪扭扭,是陈冬去年元旦送他的礼物。那天雪下得特别大,孩子们在教室里围着他唱跑调的《新年好》,陈冬把画纸攥在手里,直到最后才红着脸递过来,指尖沾着的粉笔灰蹭在他手心里,凉丝丝的。
林砚下意识把教案往抽屉里塞,指尖摩挲着硬壳封面,仿佛还能摸到那天陈冬递画时的温度。抽屉内壁粘着半片干枯的银杏叶,该是秋天落进来的,叶纹清晰得很,和望溪山上那些黄透了的银杏叶不一样——望溪的银杏叶落下来,会被孩子们捡去夹在课本里,过不了几天就软乎乎的,不像这片,还硬挺挺的,带着点中心校的冷意。他轻轻推了推教案,小太阳的边角刚好卡在抽屉松垮的锁扣上,卡得稳稳的,像陈冬当年攥着画纸不肯撒手的样子。
“刚来都得适应几天,先把这些票据理一理吧。”苏敏的声音拉回他的神思。她从桌下拖出个铁皮盒,盒盖锈了边,一打开就听见票据摩擦的沙沙声。苏敏把一摞厚厚的单据推过来,最上面一张是差旅费报销单,右下角签着张老师的名字,笔迹潦草,“张”字的撇画拉得很长。票根边缘还沾着一点白色的粉笔灰,细细的,像是从讲台抽屉里直接拿出来的,没来得及擦。
林砚拉过椅子坐下,椅垫硬邦邦的,不如望溪教学点那张旧藤椅软和。他刚坐稳,窗外突然传来清脆的上课铃,叮铃铃的声响撞在玻璃上,又弹回来,在小屋里绕了圈。他抬头望向窗外,能看见教学楼的露台,几个学生正抱着课本往教室跑,其中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跑掉了一只鞋,蹲在地上捡,旁边的男孩笑着伸手去拽她的书包带,笑声顺着风飘进财务室,脆生生的,像根细针轻轻扎在他心上。
露台上传来学生念课文的齐声朗读,“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调子齐整,却少了点什么。林砚愣了愣,才想起望溪的孩子们念课文总拖着长调,尤其是读这句时,“霜”字会拉得格外长,像山间的风,绕着教室转。此刻两种声音在他耳边叠在一起,分不清是真切还是幻觉,只觉得心口发闷,像被什么东西堵着。
他低下头,翻开第一张报销单,钢笔尖刚碰到纸张,又忍不住往抽屉瞥了眼——教案的一角露在外面,小太阳的红色在昏暗的抽屉里依旧鲜亮,像团小小的火。苏敏似乎察觉到他的走神,低头核对票据时轻声说:“之前听赵磊提过,你在望溪教得特别好,说有回下大雨,你背着学生蹚水过河去上课,学生都黏你。”
林砚捏着钢笔的手顿了顿,指腹蹭过冰凉的笔杆。他想起那天的雨,河水漫过脚踝,凉得刺骨,背上的陈冬紧紧搂着他的脖子,把脸贴在他后颈,小声说:“老师,我给你唱首歌吧。”陈冬的声音软软的,混着雨声,比此刻窗外的朗读声更清晰。他没说话,只是把那张沾着粉笔灰的报销单往面前拉了拉,用指腹顺着折痕来回抹了两遍,票根上的粉笔灰蹭在指尖,细细的,涩涩的。
以前在望溪,他总这样擦完手就去摸孩子们的头,陈冬的头发软软的,像刚晒过太阳的棉花。此刻掌心空着,只剩粉笔灰的涩感,他下意识往裤子上擦了擦,却越擦越觉得空落落的。钢笔尖在报销单的审核栏悬着,他盯着那片空白,突然看见“张老师”的签名,那“张”字的撇画明明和望溪的张校长是一个写法,却少了点校长签名时的稳重,潦草得有些仓促。
他笔尖顿了顿,墨水在纸上晕开一个小墨点。望溪的教案上,他总这样给孩子们批改作业,遇到写得好的句子,就画个小小的圆圈,墨点圆圆的,带着点温和的笑意。可此刻这墨点落在报销单上,却显得沉甸甸的,像个句号,硬生生把他的思绪从望溪拉了回来。
“怎么了?”苏敏抬头看他,手里的算盘噼啪响了两声,“是单据有问题吗?”
“没有。”林砚摇摇头,指尖攥了攥钢笔,终于在审核栏写下“属实”两个字。笔迹算不上工整,“属”字的竖钩拉得有些长,像是在纸上顿了很久才落下。写完时,他又往抽屉看了眼,小太阳依旧卡在锁扣上,安安稳稳的,像在等着他回头。
窗外的朗读声停了,换成了老师讲课的声音,透过玻璃传进来,模糊得很。苏敏的算盘声又响起来,噼啪噼啪,和账本上的数字缠在一起,成了这间小屋的底色。林砚把审核完的报销单放在一边,伸手去拿第二张,指尖刚碰到单据,就听见楼下传来孩子的哭声,尖锐又委屈。
他猛地抬头,看见露台边跑过个小小的身影,手里攥着块碎了的橡皮,哭得肩膀一抽一抽的。林砚的脚步顿了顿,差点就起身往外走——在望溪时,只要听见孩子哭,他总会第一时间走过去,要么递块糖,要么蹲下来听他们说委屈。可此刻他只是坐在椅子上,看着那个小小的身影消失在楼梯口,指尖的钢笔捏得更紧了。
苏敏顺着他的目光望出去,笑了笑:“是一年级的孩子,总为这点小事哭。咱们中心校孩子多,不比教学点清净吧?”
林砚“嗯”了一声,没多说。他想起望溪的孩子们,也会哭,却是因为丢了山里捡的野果子,或是放学时看见别的孩子有家长来接。每次他都会把哭鼻子的孩子拉到身边,从教案夹里翻出半块糖——那是他特意备着的,糖纸皱巴巴的,却总能让孩子们立刻笑起来。
他下意识去摸教案夹,指尖却碰了个空,才想起教案还在抽屉里。林砚拉开抽屉,指尖碰到教案封面的小太阳,粉笔灰的气息似乎顺着缝隙飘了出来,混着屋里的菜籽油香,竟也不觉得违和了。他轻轻把教案往抽屉深处推了推,小太阳被遮住了大半,只剩一点红色露在外面,像个小小的标记。
“对了,”苏敏突然停下手里的算盘,从抽屉里拿出串钥匙,“楼下有个储物间,你要是有东西要放,可以用这个。我去年来的时候,把冬天的厚衣服都堆在那儿了。”
林砚接过钥匙,钥匙串上挂着个小小的布偶,是只缝得歪歪扭扭的小熊,布料都起球了。“这是我侄女缝的,非要让我挂着。”苏敏笑着解释,又低头去核对账本,“你要是没事,下午可以去看看,储物间就在食堂旁边,门牌号是201。”
林砚把钥匙放在桌上,钥匙串上的小熊晃了晃,刚好对着抽屉的方向。他看着那只小熊,突然想起陈冬也给过他一个手工制品——是个用树枝编的小篮子,编得歪歪扭扭,却能装下好几块橡皮。陈冬当时说:“老师,这个给你装粉笔,你的粉笔总滚到地上。”
他拿起钥匙,指尖摩挲着冰凉的金属,突然想去储物间看看。或许,可以把教案放进去?放进去,是不是就能少想点望溪的事?可转念又觉得舍不得,那本教案里夹着太多东西了——有孩子们的画,有断成两截的粉笔,还有他写了半页的讲课思路,每一页都是望溪的日子。
窗外的阳光渐渐西斜,光斑在账本上挪了位置,落在苏敏沾着墨水渍的指尖。林砚低头翻开第二张报销单,是张文具采购单,上面写着“白色粉笔五十盒”。他看着那行字,突然想起望溪的粉笔总是不够用,孩子们会把断成小块的粉笔攒起来,偷偷塞给他。有次陈冬塞给他半块粉笔,小声说:“老师,这个我攒了好久,你别嫌小。”
钢笔尖在纸上顿了顿,林砚深吸口气,在审核栏写下“属实”。这次的笔迹比上次稳了些,只是写完后,他还是忍不住往抽屉看了眼——那点红色依旧露在外面,像颗小小的心,在陌生的办公桌里,守着他藏在心底的望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