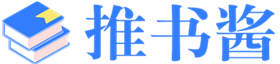梅雨季节的江南小镇,空气里永远拧得出水。青石板路湿滑黏腻,屋檐下垂挂着细密的雨帘,淅淅沥沥,没完没了,下得人心里都快要发了霉。
林夕就在这样一个沉闷的午后,第三次看见了那把红纸伞。
它就斜斜倚在镇口那座年久失修的石桥栏杆上,像一团凝固的、不合时宜的火,烧在氤氲的青灰色雨雾里。伞面是那种极鲜艳、极正的红,油纸绷得紧实,竹骨嶙峋,伞柄光滑得像是被人摩挲过无数次。桥下河水浑浊湍急,哗哗流淌,四下无人。
第一次看见,是两天前。林夕放学跑过石桥,雨正大,瞥见那抹红,心里嘀咕谁这么大意,伞落了。他没停步。
第二次,是昨天。雨小了些,那把红伞仍原封不动地待在老地方,红得刺眼。林夕放缓了脚步,多看了两眼。伞是好伞,不像被丢弃的破烂。但他心里莫名有点发毛,想起奶奶说过,路边的东西,别瞎捡。他甩甩头,跑开了。
今天是第三次。
雨几乎停了,只剩牛毛般的雨丝。那把伞还在。仿佛它就该在那里,等了很久很久。
林夕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他围着那伞慢慢踱了半圈。
真是把好伞。镇上买不到这么好的手艺。就这么扔了,太可惜。他最近正缺把结实点的伞,上学路上老淋成落汤鸡。
奶奶的叮嘱在脑子里响了一下,又迅速被这念头压了下去。一次是偶然,两次是巧合,这都第三次了,还没人来找,分明就是不要了。捡把无主的伞,能有什么事?自己吓自己。
他深吸了一口潮湿冰冷的空气,像是给自己打气,又飞快地左右瞄了一眼。
空荡荡的石桥,只有水流声。
他伸出手,指尖触到冰凉光滑的竹柄,猛地一把握住,抓起来转身就走,脚步越来越快,最后几乎是小跑起来,心口怦怦直跳,也不知是心虚还是别的什么。
那伞握在手里,分量比想象中沉。竹骨坚硬,红纸伞面微微晃动,像一只巨大的、振翅欲飞的红蝶。
他没直接回家,而是在镇子里多绕了两圈,做贼似的,直到确认绝对没人注意到他,才闪身钻进自家那条窄巷。
奶奶正坐在堂屋门口的小凳上拣豆子,老花镜滑到鼻尖。她抬起头,目光掠过林夕,以及他手里那把崭新的红纸伞,浑浊的眼睛顿了一下。
“哪儿来的伞?”老人的声音干涩,带着一种天然的警惕。
“……同学借的。”林夕喉咙发紧,把伞往身后藏了藏,不敢看奶奶的眼睛,低头快步钻回自己屋里,把伞小心翼翼塞到了床铺最底下。
奶奶没再问,只是拣豆子的动作慢了下来,眉头拧着,望着门外又开始渐渐沥沥下大的雨,叹了口气,极轻地嘟囔了一句:“这雨,怎么就没个停的时候……”
夜里,林夕做了个梦。
梦里也在下雨,很大的雨,砸在青石板上噼啪作响。他一个人站在那座石桥上,四周雾气弥漫。桥那头,模模糊糊站着个人影,很高,很瘦,穿着深色的长衫,看不清脸,手里好像也撑着把伞,伞的颜色很深,也许是黑色,也许是墨绿。
那人影似乎在看他,又似乎只是望着桥下的河水。
林夕想走过去,脚却像钉在原地。他想开口问那是谁,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只有雨声,无边无际的雨声。
还有一股极淡极淡的、若有若无的气味——像是陈年的墨汁,又混合了受潮的旧书页和某种陌生的、冰冷的香料。
他猛地惊醒,心跳如鼓,窗外雨还在下,刷刷地轻响。屋里黑得浓稠,一切轮廓模糊。他下意识地伸手摸向床底。
那把红纸伞,好端端地躺在那里。
他松了口气,却又觉得那股梦里的冷香,好像还在鼻尖萦绕了一瞬,挥之不去。
第二天,林夕醒来时头有些沉,像是没睡好。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抽出了那把伞。新伞不用,放着岂不是更怪?他这么告诉自己。
撑着红纸伞走在湿漉漉的巷子里,确实引人注目。邻居张婶提着菜篮路过,笑着打趣:“小夕,好漂亮的伞,对象送的?”
林夕脸一热,支吾着应付过去。
一整天,他都觉得有些心神不宁。上课老走神,总觉得窗外有人影晃过,仔细看却又没有。放学时雨停了,他收起伞,走着走着,忽然觉得背后发凉,猛地回头。
身后只有放学的学生和匆匆归家的路人,一切如常。
是他多心了吗?
他把伞重新塞回床底,决定明天不带了。
可是,从那天起,怪事就开始了。
先是东西莫名其妙地移位。昨晚明明放在桌上的钢笔,早上发现滚到了墙角。接着是夜里总能听到极其轻微的脚步声,窸窸窣窣,像是有谁在堂屋里踱步,凝神去听,又消失了。问奶奶,奶奶总是摇头,说人老了,耳朵背,没听见。但林夕注意到,奶奶的脸色越来越差,眼神里的忧虑越来越重。
家里那股梦里的冷香,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越来越清晰。尤其是在他的房间里,在床铺周围。
林夕开始失眠,食欲不振。他迅速消瘦下去,眼窝深陷,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青白。他不敢再碰那把伞,甚至不敢再看床底。他试过把伞扔回石桥,可每次拿起它,走到半路,不是突然肚子剧痛,就是头晕眼花,只好又原路返回。那伞像是长在了他家,怎么也丢不掉。
奶奶请了镇上的老中医来看,号了脉,只说是心神不宁,开了几服安神的药,喝了却不见好。
一个月后的半夜,林夕又被一阵极其清晰的摩擦声惊醒。
不是脚步声。
是磨墨的声音。
缓慢,均匀,带着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耐心,就在他的房门之外,堂屋的八仙桌那边。
一下,又一下。
绵密不断。
与此同时,那股冷香变得前所未有的浓烈,几乎要凝固起来,钻进他的每一个毛孔。
林夕浑身冰冷,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他把自己紧紧裹在被子里,捂得严严实实,连头都不敢露,冷汗浸透了睡衣。
磨墨声持续了很久,终于停了。
万籁俱寂。
然后,他听到了。
毛笔落在纸上的声音。
轻柔,舒缓,一笔一划,带着某种古老的韵律。
像是在写着什么。
是在写……字?
写给谁?
林夕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极致的恐惧像冰水,从他头顶浇下,冻僵了四肢百骸。他连呼吸都屏住了,整个人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不知过了多久,声音彻底消失了。那股冷香也渐渐淡去。
天快亮时,林夕才在极度的疲惫和恐惧中昏睡过去。
第二天他是被奶奶惊恐的叫声吵醒的。
他连滚带爬地冲出去。
奶奶站在堂屋中央,脸色惨白如纸,手指颤抖地指着靠墙的那张老旧的八仙桌。
暗红色的桌面上,昏黄的晨光中,赫然呈现着几行墨迹!
那墨色新润,尚未干透,泛着幽光。字迹是一种极其古拙、瘦硬的隶书,工工整整,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阴冷之气——
“寒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
一首送别诗。
墨迹在最后一句末尾微微顿住,拖出一条极细的墨丝,仿佛写字的人在此停笔,沉吟不语。
空气里,那股冷香顽固地残留着。
奶奶猛地转过身,枯瘦的手死死抓住林夕的胳膊,指甲几乎掐进他肉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伞!是不是那把伞?!你跟我说实话!那伞到底哪来的?!”
林夕看着那墨字,看着奶奶惊恐欲绝的脸,最后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了。他腿一软,瘫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断断续续说出了石桥捡伞的经过。
奶奶听完,身子晃了晃,脸上最后一点血色也褪尽了。她喃喃道:“讨债的……是讨债的找上门了……那是‘送魂伞’啊……收了伞,就是应了约……它要送你走了……”
老人猛地推开林夕,疯了一样冲进里屋,从箱底翻出几沓粗糙的黄纸钱,又找出几炷颜色陈旧的线香,冲到院子里,不顾还在飘落的雨丝,噗通一声跪在湿冷的泥地里,点燃纸钱和香,一边磕头一边哭喊,语无伦次:
“大人有大量……孩子小……不懂事……冲撞了您……求您高抬贵手……放过我孙子……我们给您烧纸……给您念经……求求您……求求您了……”
纸钱在潮湿的空气里燃烧得很慢,冒出浓白的烟,扭曲着上升,散发出呛人的气味。香火头明灭不定。
林夕瘫坐在堂屋门口,看着奶奶佝偻的背影在雨和烟灰中颤抖,看着桌上那几行冰冷的墨字,巨大的恐惧和悔恨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紧了他的心脏,让他无法呼吸。
奶奶的哀求声和哭泣声在淅沥的雨声中显得异常微弱,无助。
当夜,奶奶发起了高烧,胡话不断,反复念叨着“伞”、“走开”、“别碰我孙子”。
请了大夫来看,说是急火攻心,又受了风寒,开了药,让好生养着。
林夕守在奶奶床前,愧疚和恐惧像两条毒蛇啃噬着他。他一夜未眠。
天快亮时,奶奶的烧似乎退了一点,昏昏沉沉地睡去。林夕实在撑不住,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自己房间,一头栽倒在床上,几乎是瞬间就陷入了昏睡。
他又做梦了。
这次梦格外清晰。
还是在石桥,雨大得惊人,天地间白茫茫一片。桥那头,那个穿着深色长衫的高瘦人影变得清晰了些,依然看不清面容,但能看见他手里撑着的,正是一把墨绿色的油纸伞。
那人影朝他招了招手。
然后,缓缓地,转过身,向着桥的另一端,镇子外的方向走去。
像是在引路。
林夕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动了起来,跟着那墨绿色的伞影,一步步往前走。
冰冷的雨水打在他脸上,他却感觉不到冷。桥下的河水奔腾咆哮。
就在他要走下石桥的那一刻,
他猛地惊醒!
胸口剧烈起伏,冷汗淋漓。
窗外,天光微亮,雨声渐歇。
他喘着气,下意识地扭头看向床底——
那把红纸伞,不见了。
林夕的心猛地一沉,一种极其不祥的预感攫住他。他连滚带爬地冲下床,跌跌撞撞地跑向奶奶的房间。
“奶奶!伞不见了!”
房间里空无一人。
被子掀开一半,床上没人。
“奶奶?”林夕的声音开始发颤,他冲出堂屋,院子里也没有。
一种冰冷的绝望瞬间淹没了他。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发疯似的冲出家门,朝着镇口石桥的方向狂奔。
清晨的小镇还在沉睡,青石板路湿滑,寂静无声。
他跑得肺都要炸开,心脏狂跳,几乎要冲破胸膛。
远远地,他看见了石桥。
桥上,空空如也。
只有桥栏杆上,湿漉漉地挂着几滴未干的水珠。
林夕的脚步慢了下来,一步一步挪上石桥,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越收越紧。他扶着冰凉的桥栏杆,大口喘着气,目光绝望地扫视着四周。
没有人。
没有奶奶。
也没有伞。
河水在桥下呜咽着流淌。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那段曾经三次倚放过红纸伞的桥栏杆上。
那里,似乎比别处更干净一些。
栏杆下的青石桥面上,放着一小堆东西。
林夕的瞳孔骤然收缩。
他慢慢地、慢慢地走过去,像是走向刑场。
那是奶奶昨晚烧剩的几炷颜色陈旧的线香,湿漉漉地堆在那里,香头黑黢黢的。
旁边,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双奶奶平时穿的黑布鞋。鞋底干干净净,像是仔细擦过,一点泥泞都不沾。
而最让林夕浑身血液冻住的,是那双布鞋旁边,用香灰工工整整写着的几个字。那字迹瘦硬古拙,和昨夜桌上墨迹一模一样,在湿漉漉的桥面上依然清晰可辨——
“人,我送走了。” “伞,两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