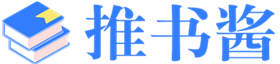第72小时播报是一本备受好评的悬疑脑洞小说,作者韦大鱼以其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描绘,为读者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小说的主角林野勇敢、善良、聪明,深受读者们的喜爱。目前,这本小说已经连载,最新章节第12章更是引人入胜。如果你喜欢阅读悬疑脑洞小说,那么这本书一定值得一读!主要讲述了:林野的手从控制面板滑下,指尖蹭过最后一簇火花。那点蓝光像垂死的萤火虫,在他指缝间熄灭。灯一盏接一盏暗下去,仿佛被人无声地吹灭。电梯门合拢,吱——嘎,像是某种巨兽闭上了嘴。屏幕彻底黑了,只剩一行字浮在玻…

《第72小时播报》精彩章节试读
林野的手从控制面板滑下,指尖蹭过最后一簇火花。那点蓝光像垂死的萤火虫,在他指缝间熄灭。灯一盏接一盏暗下去,仿佛被人无声地吹灭。电梯门合拢,吱——嘎,像是某种巨兽闭上了嘴。屏幕彻底黑了,只剩一行字浮在玻璃上:“身份验证失败”,像是有人用粉笔写过又擦去,可痕迹还在。
他没动。
背贴着井壁,冰冷的金属硌着骨头。整栋楼的重量仿佛全压在他脊梁上。左臂那道疤又开始发烫——不是灼烧,而是皮下在跳,一下一下,像心跳,又像有人在肉里敲摩斯密码。三年前动过手术,切口早已愈合,可总觉得里面还埋着什么,没清干净。
低头看手。
钥匙仍攥在掌心,齿缝里嵌着黑血,结成硬壳,边缘泛红,像铁锈。这把钥匙,他试了七次电梯,每一次都失败。最后一次启动时,系统跳出一串乱码,整层楼的应急灯闪了一下,像是抽搐。他不再试了。不是认命,是明白了——这栋楼,已经不认他了。
转身,往上走。
楼梯间的铁管冰冷,焊口裂得七零八落,像被野兽啃咬过。空气里弥漫着铁锈味,混着霉烂的酸气。每踩一级台阶,脚底都震一下。不是他踩的,而是从楼体深处传来的震动——底下有重物在撞击,一下一下,如同地基里有人在敲钟。
他数着台阶。
三十七级。和通风管口刻的数字一样。这个数他记得太清楚。三天前,他在202室通风口外的检修盖上见过它,红漆写的,歪歪扭扭,像逃命时匆忙划下的记号。当时没在意,以为是工人乱画。现在,它又出现在这里,仿佛在说:你走的每一步,它都记着。
三十七级到头,六楼走廊。
601的门牌挂在锈钉上,“6”字歪斜,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顶弯了。门缝底下渗出黑红色黏液,缓缓爬行,像凝固的血重新活了过来。林野站着,没有推门。抬起左手,掌心那个Ω形的疤痕猛地一跳,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推门。
门轴尖啸,如同多年未开的棺盖。屋里静得异常。没有菌丝蠕动的沙沙声,没有墙内电流的嗡鸣,连空气都像冻结了。桌上摊着那本乐谱——202室钢琴老师留下的《致爱丽丝》手抄本。纸页泛黄,边缘卷曲,右上角一块咖啡渍,形状像一只眼睛。
他认得这本子。
三天前,在钢琴凳的暗格里找到的。那时楼还在“活”,走廊灯每七分钟闪一次,电梯还能下到B2,菌丝只在墙角蔓延。他翻过一遍,以为只是个普通女人练琴的笔记。可现在,它摊在这里,像一封未写完的遗书。
第19小节被红笔圈了出来。
三个字歪歪扭扭写在空白处:“快逃”。
字是新的。墨迹未干,边缘晕开,像是刚写上去的。他蹲下,指尖触碰那行字,纸面微潮,墨里混着黏腻的东西。凑近闻了闻——不是墨香,是铁腥味,还带着一丝苦涩,像神经药剂。和门缝里渗出的黑血气味一模一样。
猛地抬头。
墙上挂钟的分针正指着7。
秒针一格一格走着,“咔哒”,像倒计时。他盯着,呼吸放轻。三秒后,楼下“咚”地一声。
重物砸地,从四楼传来,方向精准。他没动,继续看着钟。七分钟后,分针再次回到7,声音如期而至,分毫不差。
第三次,他掏出那本烧焦的笔记本——从B1废墟里扒出来的,封面焦黑,内页残缺。撕下一页,在背面用炭灰写下:
“7:00,7:07,7:14”
每一笔都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记得。三年前,“深井计划”值夜班,每天七点整,设备会自动记录一次“结构异动”。他填日志,格式固定:时间、频率、震源深度、异常值。如今这串数字,和当年完全一致。
他撕下那页乐谱。
红笔写的“快逃”被撕开,纸“嘶”地裂开。就在纸片离手的瞬间,整本乐谱突然翻页。
哗啦啦,没人碰,没有风,书脊也没晃动,可纸页像被无形的手翻过,停在一页空白。
一行字浮现出来。
不是写出来的,是渗出来的。暗红,湿漉漉的,像刚从血管里挤出。字迹歪斜,笔画带钩,像是用指甲划的:
“他们能听见”
他伸手,指尖沾上铁腥。不是墨,是血。立刻认出来了——铁锈、神经药残留,还有一丝怪味,和302室药柜底层那瓶过期胃药一样。妹妹失踪前的病历里见过这配方,代号“镇静-7”,治癫痫,副作用是幻听。
猛地抬头。
五楼传来咳嗽。
三短,一长,停顿,再三短。
王叔的节奏。
他听了一辈子。王叔住502,有哮喘,每天六点咳醒,声音顺着通风管传下来,像老机器喘气。小时候常被吵醒,后来竟能在梦里分辨这节奏。
可现在,不止一个方向。
左边墙里,右边天花板,脚下地板,三处同时响起,节奏一致,声音相同,像被复制后同步播放。没有延迟,没有回声,不合常理。这栋楼,在“复制”声音。
他屏住呼吸,贴上门。
猫眼被堵死了,黑红菌丝缠绕,像血栓。他掏出一片铝箔——302室药盒上撕下来的,卷着边,带着药片压痕。展开,对折,指甲压出反光面,贴在猫眼旁,斜着看。
空的。
水泥地,墙皮剥落,铁门缝渗着黏液。没有影子,没有动静。可咳嗽声还在,三短一长,循环往复,像在测试信号。
他蹲下,将铝箔贴在通风管口。
震动传来。不是风,是金属在共振。咳嗽声顺着管道传播,被楼体复制、放大、分发到各层。整栋楼成了共鸣箱,通风管是它的声带。
忽然想起202室的钢琴。
自动弹奏,信号发射器藏在琴盖下。军用级,能干扰生物电。如果钢琴是“发”,那这栋楼就是“收”。
而他,是唯一听懂的人。
回到桌边,摊开乐谱,四角压上重物——消防斧、钥匙、烧焦的电路板、半截琴弦。纸页不再晃动。他点燃半张寻人启事,火苗蓝绿,烧得安静,像化学反应。凑近血字,热气一烘,墨迹鼓起,仿佛活了过来。
“他们能听见”。
听见什么?
低头看手。红笔字笔压不均,像是写时手在抖。可“7”被反复描粗,不是恐惧,是强调。是提醒。
翻到前页。
角落有铅笔小字:“练习用,第17遍”。字迹工整,日期:三年前10月16日。妹妹失踪的前一天。
他想起来了。
那天601传来琴声,弹的是《致爱丽丝》,但节奏乱了,第七个音拖了半拍。他以为是练错了,没在意。现在才明白——不是错,是信号。通风管里的咳嗽也是,第七个音总是慢0.3秒。
和那天的琴声,一模一样。
合上乐谱,手指卡在书脊,纸边割破皮肤,血珠渗出,滴在“他们能听见”上。
血没有晕开。
被吸进去了,像纸在喝水。
字变了。
“他们能听见你”
他猛地合上本子,斧头砸向桌角,震得钥匙跳起。火灭了,屋里陷入黑暗。只有挂钟还在走,秒针一格一格,像在倒数。
盯着门缝。
黏液继续爬行,从门底渗出,沿地板蔓延,不是乱流,而是成线、弯折、连接,最后拼出一个符号——和他掌心Ω疤痕正好相反。
℧。
反的。
他懂了。
这栋楼没死。它在记录。记录每个人的举动、呼吸、心跳。它把声音编成谱,把血写成字,把死亡排成节拍。202室的钢琴不是开始,是回放。所有弹奏,都是重演。
“快逃”不是警告。
是上一个死在这里的人,留下的最后一个音。
他抓起乐谱想撕。手一用力,纸竟发烫,烫得他松手。书落回桌面,自动翻回那页。血字蠕动,笔画拉长,重组。
新字浮现:
“你已经弹了十二个音”
他没动。
心跳撞击耳膜。十二个音。不是比喻,是计数。
他从202室取信号发射器,一。
撬开琴盖,二。
卡住琴槌,三。
拓印蜡笔画,四。
抛出哮喘喷雾瓶,五。
塞进排水管,六。
用孕妇装按掌印,七。
劈开菌丝,八。
撑开门缝,九。
模拟呼吸,十。
取下假牙,十一。
拼合寻人启事,十二。
每一个动作,都像按下琴键。
第十三个,还没安。
抬头看钟。
分针指向12。
秒针走完最后一格,楼体震了一下。不是坠物,是结构在调整。像机器走完十二步,等待最后一道指令。
五楼的咳嗽停了。
走廊死寂。
他盯着乐谱,血字仍在变化。
笔画拉长,扭曲,最终拼出三个字:
“现在听”
林野慢慢跪下,手掌贴地。
地板冰冷,但他感觉到,地底传来微弱震动,像心跳,又像低频信号。闭上眼,耳朵被寂静填满。就在那一瞬,他听见了。
不是声音。
是频率。
介于听见与听不见之间,像老收音机调频的杂音,又像神经放电的噼啪。它从通风管渗出,从墙缝钻入,从地板下升起,最终汇成一段旋律。
《致爱丽丝》。
但不是正序。
是倒放的。
每个音被拉长、扭曲,第七个音无限延展,像绷到极限的弦,即将断裂。旋律中夹杂着断续的呼吸、脚步、金属摩擦,还有——一声尖叫。
他认得。
妹妹的。
三年前,监控最后画面,她在B2走廊回头,嘴张着,像在喊。音频损坏,只剩杂音。现在,这段旋律里,她的声音回来了。
“哥……别进来……”
旋律继续。
王叔的咳嗽被编成节奏,三短一长,像节拍器。202室钢琴自动弹奏,音符错乱,却与咳嗽形成和声。后来,电梯坠落的轰鸣被压成低音和弦,贯穿全曲。
一首“死亡交响曲”。
记录所有死在这栋楼里的人的最后一刻。
而他,是第十三个音的触发者。
睁眼,看挂钟。
秒针停了。
分针仍指12。
可他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这栋楼,已不在现实世界里。
它有自己的节拍。
他慢慢站起,走向门。
门外,黏液拼成的℧符号开始蠕动,收缩、变形,最终化作一串数字:13。
低头看手。
钥匙还在。掌心的Ω疤痕发烫,像在回应什么。
他知道,第十三个动作,得由他来完成。
不是逃。
不是藏。
是“弹”。
转身,走向乐谱。
翻开,寻找空白页。
掏出那支烧焦的炭笔——从B1火灾中捡出,笔芯里嵌着半片电路板。用尽全力,写下三个字:
“我听见”
笔尖划过纸面的瞬间,整栋楼猛然震动。
挂钟玻璃炸裂,秒针飞出,钉入墙壁。
通风管轰鸣,咳嗽声再起,可这次,不再是三短一长。
是一长,三短。
反的。
楼在重组,钢筋扭曲,水泥开裂,像巨兽苏醒。六楼地板塌陷,裂缝如蛛网般蔓延,露出下方无尽的黑暗。可那黑暗中,有光。
蓝绿色的,像实验室的应急灯。
他看见了。
B2。
三年前的实验室,完好如初。
玻璃墙后,妹妹站在操作台前,手里拿着乐谱,抬头看他,嘴唇微动。
“现在,轮到你了。”
他迈出一步。
地板塌陷,他坠入黑暗。
下坠中,耳边响起旋律。
《致爱丽丝》正序版,清清楚楚,每一个音都准确无误。
第七个音,不再拖拍。
他闭上眼,任身体下坠。
他知道,这栋楼不会让他死。
它要他“继续弹”。
黑暗中,落地。
不是水泥地。
是柔软的地毯。
睁眼,202室。
钢琴静静伫立,琴盖微启,露出内部机械结构。琴键洁白,仿佛从未被触碰。墙上挂钟,分针指向7。
他又回来了。
可他知道,这不是循环。
是重置。
走向钢琴,掀开琴盖。
信号发射器还在,军用级,编号“深井-7”。他伸手取出,握在掌心。掌心的Ω疤痕剧烈跳动,与设备共振。
低头看乐谱。
不知何时已回到手中,翻开那页,血字变了:
“你已经弹了十三个音”
他笑了。
笑得很轻,像终于明白了什么。
把发射器放回钢琴,合上琴盖。
坐下。
手指落在琴键上。
第一个音落下。
《致爱丽丝》第一音,清亮。
整栋楼,静了一瞬。
接着,通风管传来回音。
咳嗽、脚步、菌丝蠕动、电梯声响,全都汇入旋律,成了伴奏。
他继续弹。
第二音,第三音……
每弹一个,楼就震一下。
不是毁灭。
是共鸣。
他知道,这栋楼不是牢笼。
是乐器。
他是唯一的演奏者。
妹妹的声音从通风管传来,轻轻说:
“这次,别弹错。”
他点头,手指微动。
第七个音,准时落下。
没有拖拍。
旋律完整。
整栋楼,开始发光。
从地基到楼顶,钢筋、水泥、通风管,全都泛起蓝绿微光,像神经网络活了过来。
他继续弹。
弹到第十二音,挂钟的秒针重新开始走动。
第十三音落下,楼体猛震,随后,归于寂静。
门开了。
不是601。
是楼外的大门。
阳光照进来。
他站起,走出钢琴室,穿过走廊,下楼,推开单元门。
外面,街道空无一人。
可他知道,有人在等。
抬头看天。
云层裂开一道缝隙,阳光如柱,照在他掌心。
Ω疤痕消失了。
取而代之,一行极小的字,刻在皮肤上:
“演奏者已登记”
深吸一口气,迈步走出。
身后,楼门缓缓合上。
没有上锁。
只是轻轻关上。
像一首曲子,终于画上休止符。
可他知道,音乐不会停止。
只是换了个地方,继续演奏。
他摸了摸口袋。
乐谱还在。
翻开,最后一页,多了行字:
“下次,换首曲子”
他笑了。
走向阳光深处。
三日后,深夜。
某栋旧居民楼五楼。
一扇窗,透出昏黄灯光。
桌上摊着一本发黄的乐谱。
《致爱丽丝》。
第19小节被红笔圈了。
三个字歪歪扭扭写在空白处:
“快逃”
窗外,风停了。
屋里,钢琴无人触碰,却突然响起一个音。
清脆,孤寂。
像在召唤。
像在等待。
下一个演奏者。
小说《第72小时播报》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