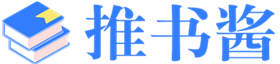金莲川的夏天,能把人晒出三层油!
风裹着草香往帐篷里钻,忽必烈光着膀子坐在地毯上,手里攥着半块烤羊腿,正跟刘秉忠下棋——准确说,是刘秉忠在下,他在瞎指挥。
“跳马!跳马啊!”忽必烈嚼着羊肉,含糊不清地喊,“你看他那个炮,都快怼到你老将脸上了!”
刘秉忠穿着件灰布僧袍,慢悠悠地挪了个卒:“王爷,下棋如治国,得沉住气。卒子虽慢,走对了也能将军。”
“可我这马快啊!”忽必烈急得拍大腿,羊油顺着指缝往下滴,“你看旭烈兀,昨天追黄羊,跑得多快!”
正说着,帐篷帘子“哗啦”被掀开,旭烈兀顶着一头草屑冲进来,手里举着个歪歪扭扭的稻草人:“哥!你看我做的靶子!等会儿咱们去射箭!”
忽必烈一看那稻草人,差点笑喷——脑袋是用南瓜做的,眼睛画成两个黑圈,身上裹着旭烈兀穿小了的红布袍,活像个刚从灶膛里爬出来的小鬼。
“你这靶子,射着都嫌扎眼!”忽必烈把羊腿骨扔给帐外的狗,“先别射箭,赵璧先生说今天有贵客来,你赶紧把身上的草屑拍干净,别让人笑话!”
“贵客?”旭烈兀眼睛一亮,赶紧拍身上的草,“是会做红烧肉的贵客吗?上次王鹗先生做的红烧肉,我还没吃够呢!”
提到王鹗,忽必烈心里就美滋滋的——自从征贤令发出去,来投奔的人就跟夏天的草似的,一茬接一茬。王鹗来了,赵璧早就在这儿,刘秉忠更是常驻,今天要来的,是赵璧特意写信请来的姚枢,听说肚子里的学问能装三车书!
“别光想着吃!”忽必烈敲了下旭烈兀的脑袋,“姚枢先生是大儒,人家懂的是治国平天下,不是红烧肉!”
“懂治国也能懂做饭吧?”旭烈兀不服气,“上次张文谦先生来,不就带了自己种的土豆?还教老哈达做土豆炖肉,可香了!”
正说着,老哈达端着奶茶进来,听见这话,赶紧接茬:“可不是嘛!张先生那土豆炖肉,我学了三回才学会!二王子一顿吃了两大碗,连汤都喝光了!”
旭烈兀脸一红,赶紧转移话题:“老哈达,今天有啥好吃的?我闻见烤羊肉的香味了!”
“早给您烤着呢!”老哈达笑着说,“还有刚煮好的奶酒,等会儿贵客来了,咱们一起喝!”
话音刚落,帐外传来马蹄声,还夹杂着说话声。忽必烈赶紧穿上皮袍,整理了一下衣领:“来了!走,去迎迎!”
一出门,就看见赵璧陪着个穿青布儒衫的人走过来。那人五十来岁,头发用木簪挽着,背着个比他人还高的书箱,走路稳稳当当,一看就是个读书人。
“王爷!这位就是姚枢先生!”赵璧笑着介绍。
姚枢赶紧躬身行礼,动作标准得像提前练过八百遍:“草民姚枢,拜见忽必烈王爷。”
“快起来!快起来!”忽必烈赶紧扶住他,眼睛直往书箱上瞟,“先生这书箱里,装的都是宝贝吧?”
姚枢笑了:“回王爷,都是些圣贤书,算不上宝贝,但要是能给王爷治国帮上忙,那就是它们的造化了。”
“说得好!”忽必烈拍手,“走,进帐里聊!老哈达,赶紧把奶茶端上来,再切盘最好的奶皮子!”
刚进帐,旭烈兀就凑到姚枢身边,踮着脚看他的书箱:“先生,你这箱子里有菜谱吗?就是能做红烧肉、土豆炖肉的那种?”
姚枢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二王子说笑了,草民箱子里都是书,没有菜谱。不过草民倒是会做几道家常菜,要是二王子不嫌弃,改日给您露一手?”
“真的?!”旭烈兀高兴得跳起来,“那我要吃红烧肉!还要吃糖醋鱼!上次听王鹗先生说,糖醋鱼是甜的,我还没吃过呢!”
忽必烈无奈地摇了摇头:“你这孩子,就知道吃!姚先生是来给咱们讲治国之道的,不是来当厨子的!”
“治国也得吃饭嘛!”旭烈兀梗着脖子,“娘说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要是老百姓都没饭吃,还怎么治国?”
这话一出,帐里的人都笑了。姚枢点头:“二王子说得在理!治国先治食,百姓有饭吃,天下才能安。草民这次来,还带了些汉地的谷种,要是王爷不嫌弃,咱们可以在金莲川试试种庄稼。”
“种庄稼?”忽必烈眼睛一亮,“能种出比草原上的草还壮的庄稼吗?”
“当然能!”姚枢说,“汉地的谷子,一亩地能收好几石!要是种得好,咱们的士兵就有吃不完的粮食,不用再靠打猎过日子了!”
“那赶紧种!”忽必烈急着说,“老哈达,明天就找块好地,跟着姚先生学种庄稼!”
老哈达赶紧应道:“哎!我这就去准备!”
正热闹着,帐外又有人喊:“王爷!张文谦先生和窦默先生来了!”
忽必烈更高兴了:“快请进来!今天这是啥好日子,贤才都凑一块儿了!”
张文谦和窦默一前一后走进来。张文谦手里提着个布袋子,里面鼓鼓囊囊的,一看就是又带了什么好东西;窦默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袍,手里拿着个小本子,边走边记,活像个怕漏了知识点的学生。
“王爷!”张文谦把布袋子递过去,“这是我新培育的菜籽,种出来的白菜又大又嫩,冬天腌成酸菜,能吃一整个冬天!”
窦默也把小本子递过来:“王爷,这是草民整理的《农桑辑要》节选,里面记了汉地种庄稼的技巧,您要是感兴趣,草民给您讲讲。”
忽必烈接过布袋子和小本子,笑得合不拢嘴:“好!好!有你们在,我这金莲川就热闹了!老哈达,再去烤只羊!今天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旭烈兀在旁边听着,突然问:“张先生,你这菜籽能种出烤羊腿吗?”
帐里的人又笑了。张文谦忍着笑说:“二王子,菜籽种不出烤羊腿,但种出的白菜,能跟烤羊腿一起炖,可香了!”
“那也行!”旭烈兀点点头,又转向窦默,“窦先生,你那本子里有红烧肉的做法吗?”
窦默愣了一下,然后认真地说:“二王子,本子里记的是农桑,不是菜谱。不过草民知道有家馆子做红烧肉特别好吃,等以后去汉地,草民带您去吃。”
“真的?!”旭烈兀赶紧拉着窦默的手,“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我现在就想去!”
忽必烈赶紧把旭烈兀拉开:“别胡闹!窦先生刚到,还没歇着呢!先让先生喝口奶茶,吃点烤羊肉!”
接下来的几天,金莲川的营地就跟赶庙会似的,天天热闹非凡。
姚枢每天带着老哈达和几个士兵种庄稼,教他们翻地、施肥、浇水。旭烈兀天天跑去看,一开始还好奇地帮着浇水,结果把水浇多了,差点把种子淹死。姚枢哭笑不得,只好让他负责“驱赶鸟雀”——其实就是让他在田埂上玩,别捣乱。
张文谦则忙着整理漠南汉地的户籍和赋税。他带着几个助手,天天趴在桌子上算账,算得头发都白了几根。忽必烈有时候会去看他,每次都被满桌子的账本吓一跳:“张先生,这得算到什么时候啊?”
张文谦推了推鼻梁上的木框眼镜(这是他特意从汉地带过来的,说是能看清小字):“王爷,快了!等算清楚了,咱们就能知道哪些地方赋税重,哪些地方需要救济,也好制定政策。”
窦默则忙着给忽必烈和营地里的人讲经。他讲《论语》《孟子》,讲“仁政”“爱民”,讲得头头是道。就是语速太慢,每次讲不到一半,旭烈兀就开始打瞌睡,脑袋一点一点的,像小鸡啄米。
有一次,窦默讲“仁者爱人”,讲得正投入,突然听见“咚”的一声——旭烈兀头撞到了桌子上,醒了过来,还迷迷糊糊地问:“先生,讲到红烧肉了吗?”
帐里的人都笑了。忽必烈赶紧戳了戳旭烈兀的胳膊:“别瞎问!认真听!”
窦默也笑了:“二王子要是困了,就先去歇会儿。等草民讲完了,再跟您聊红烧肉。”
旭烈兀一听,立马坐直了:“我不困!我认真听!”结果没坚持三分钟,又开始点头。
刘秉忠和王鹗则忙着帮忽必烈规划幕府。他们在金莲川的中心地带建了几间大帐篷,一间用来开会,一间用来放书,还有一间用来招待客人。帐篷外面挂着块木牌子,上面是王鹗写的“金莲川幕府”四个大字,写得龙飞凤舞,特别气派。
忽必烈看着越来越热闹的幕府,心里别提多高兴了。他每天早上起来,先去田地里看姚枢种的庄稼,然后去张文谦那儿看账本,中午跟大家一起吃烤羊肉,下午听窦默讲经,晚上再跟刘秉忠、王鹗他们讨论治国之道。日子过得充实又有趣,比在草原上打猎还过瘾!
这天,赵璧突然对忽必烈说:“王爷,现在幕府人才济济,您又这么重视儒学,汉地的儒生们都很敬佩您。不如您就接受‘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这样既能彰显您对儒学的尊崇,也能吸引更多贤才来投。”
“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愣了一下,“这称号厉害吗?比‘草原第一射手’还厉害?”
“当然厉害!”赵璧说,“‘草原第一射手’只能射猎物,‘儒教大宗师’能得到天下读书人的认可,能让更多人愿意跟着您干!”
“那行!”忽必烈一拍大腿,“我接受!什么时候办仪式?我得让旭烈兀也来看看,让他知道,除了打猎,还有更厉害的事!”
办仪式那天,金莲川的营地张灯结彩,热闹得像过节。
姚枢和王鹗一起写了篇《儒教大宗师颂》,准备在仪式上念;张文谦特意做了件新的儒衫,穿在身上精神抖擞;窦默则准备了一本《论语》,要送给忽必烈当礼物;刘秉忠还特意从附近的寺庙里请了几个僧人,来吹奏乐器烘托气氛。
旭烈兀也没闲着,他找老哈达一起编了个花环,想用草原的方式给忽必烈“加冕”。结果花环编得太大,套在忽必烈头上差点掉下来,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仪式开始了。姚枢站在台上,手里拿着《儒教大宗师颂》,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他的声音洪亮,念得特别有气势,听得台下的人都热血沸腾。
忽必烈穿着一身崭新的蒙古袍,腰间系着父亲留下的马鞭,手里捧着窦默送的《论语》,站在台上,心里既激动又紧张——他还是第一次接受这么隆重的称号,比当年祖父成吉思汗夸他箭法好还高兴!
念完颂词,赵璧走上台,手里拿着一顶用竹篾和丝绸做的“儒冠”,要给忽必烈戴上。这顶儒冠是王鹗特意设计的,既保留了汉人的样式,又在上面绣了蒙古人喜欢的狼图腾,特别别致。
忽必烈弯腰,让赵璧把儒冠戴上。刚戴好,旭烈兀就跑上台,把那个花环套在他脖子上:“哥!这是我给你编的花环!比那个帽子好看!”
台下的人又笑了。忽必烈也笑了,摸了摸旭烈兀的头:“好!都好看!”
仪式结束后,大家一起吃烤全羊、喝奶酒,热闹到半夜。姚枢和窦默还现场写了几首诗,歌颂忽必烈重视贤才、尊崇儒学的举动;张文谦则跟大家聊起了未来的治国计划,说要在漠南汉地兴修水利、开办学校;刘秉忠则跟忽必烈聊起了天文历法,说要编一本适合草原和汉地都用的日历。
旭烈兀吃得肚子滚圆,坐在旁边听他们聊天,虽然很多话听不懂,但看着大家高兴,他也跟着高兴。他偷偷对忽必烈说:“哥,现在咱们幕府这么多人,以后肯定能吃到更多好吃的!”
忽必烈敲了下他的脑袋:“就知道吃!这些先生都是来帮咱们治国的,不是来给你做吃的!”
“治国也得吃啊!”旭烈兀不服气,“要是大家都没饭吃,怎么治国?”
这话又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姚枢笑着说:“二王子说得对!民以食为天,咱们治国,首先就得让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等以后咱们把漠南汉地治理好了,二王子想吃什么,都能吃到!”
“真的?!”旭烈兀眼睛一亮,“那我要吃红烧肉、糖醋鱼、土豆炖肉、白菜炖羊肉……”
他一边数,一边掰手指头,数到最后,手指头都不够用了,引得大家笑得更欢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金莲川幕府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仅汉地的贤才纷纷来投,就连草原上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听说忽必烈重视人才、善于治国,想来投奔。
这天,又有一个叫郝经的汉人书生来投。他带着自己写的《便宜新政》,里面详细写了如何治理漠南汉地的办法,忽必烈看了之后,高兴得睡不着觉,当即任命郝经为幕府的参军,让他跟着张文谦一起处理政务。
幕府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分工明确:姚枢负责农业,张文谦负责财政,窦默负责教育,王鹗负责文书,刘秉忠负责规划,郝经负责参谋……一个融合了蒙汉精英的智囊团,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忽必烈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他不再是那个只会骑射的草原王子,而是开始学着如何当一个好的统治者,如何让漠南汉地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常常跟大家说:“以前我觉得,草原上的硬弓最厉害,能射倒最壮的黄羊,能打败最凶的敌人。现在我才知道,贤才的智慧比硬弓还厉害,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能让天下太平。”
大家听了,都纷纷点头。姚枢说:“王爷能有这样的觉悟,是漠南汉地老百姓的福气!”
张文谦也说:“只要王爷坚持重视贤才、尊崇儒学,咱们肯定能把漠南汉地治理好,给大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忽必烈心里也这么想。他觉得,有这么多贤才帮着自己,别说治理漠南汉地,就算是治理整个天下,也不是不可能!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金莲川幕府的盛况,已经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和林,飞到了大汗蒙哥的耳朵里。
和林的汗帐里,蒙哥正坐在宝座上,手里拿着一封密报,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这封密报是漠北的一个贵族送来的,上面写得清清楚楚:忽必烈在金莲川广招汉地贤才,如今幕府已有数十人,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忽必烈每日与这些汉人讲经论史,还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行事越来越像汉地的皇帝;更有甚者,忽必烈还在漠南汉地兴修水利、开办学校,收拢民心,似有自立之心……
蒙哥越看越生气,把密报往桌子上一拍,吓得旁边的近侍赶紧跪下。
“忽必烈!”蒙哥的声音又冷又硬,“他忘了自己是蒙古人了吗?天天跟南人混在一起,学南人的玩意儿,还接受什么‘儒教大宗师’的称号!他想干什么?”
近侍不敢抬头,小声说:“大汗,或许……或许四王爷只是想把漠南汉地治理好,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意思?”蒙哥冷笑一声,“他身边聚集了这么多汉人,个个都有本事,要是他真有别的心思,谁能拦得住他?!”
他站起身,走到帐门口,望着南方——那是金莲川的方向。阳光照在他的脸上,却没带来一丝暖意。
“传我的命令,”蒙哥的声音低沉而有力,“派人去金莲川,名义上是‘慰问’忽必烈,实际上是去看看他到底在干什么!要是他真有不臣之心,别怪我这个做大哥的,不念兄弟情分!”
“是!”近侍赶紧应道,起身匆匆忙忙地去传令了。
汗帐里只剩下蒙哥一个人。他站在那里,眉头紧锁,心里五味杂陈——忽必烈是他的四弟,小时候两人一起在草原上打猎,一起在祖父成吉思汗的帐里听故事,感情一直很好。他之所以任命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事,就是因为信任他,觉得他“最长且贤”,能把事情办好。
可现在,忽必烈的所作所为,却让他越来越看不懂,越来越担心。
他真的会忘了蒙古的传统,忘了自己的身份吗?
他身边的那些汉人,真的只是来帮他治国的吗?
还是说,他们想利用忽必烈,在漠南汉地建立自己的势力?
蒙哥不知道答案。但他知道,必须尽快弄清楚真相,否则,大蒙古国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乱子。
而此时的金莲川,还沉浸在热闹和喜悦之中。
忽必烈正和刘秉忠、姚枢、张文谦他们一起,站在田地里,看着姚枢种的庄稼。绿油油的谷子长得比膝盖还高,风一吹,“哗啦啦”响,像在唱歌。
“姚先生,你看这谷子,什么时候能收割?”忽必烈笑着问。
姚枢也笑着说:“回王爷,再过两个月就能收割了!到时候,咱们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谷子了!”
“太好了!”忽必烈拍手,“等收割的时候,咱们要好好庆祝一下!让大家都尝尝咱们自己种的粮食!”
张文谦也说:“王爷,等谷子收割了,咱们就可以在漠南汉地推广种植,让更多老百姓都能吃上谷子!”
刘秉忠则说:“王爷,粮食有了,下一步咱们就可以兴修水利、开办学校了。只要咱们一步一步来,漠南汉地肯定能越来越好!”
忽必烈点点头,心里充满了期待。他看着眼前绿油油的庄稼,看着身边意气风发的贤才,觉得未来一片光明。
他完全不知道,一股无形的压力,正从和林方向,悄悄地向金莲川蔓延。
那股压力,像草原上的暴风雨,来得悄无声息,却可能在不经意间,摧毁他现在拥有的一切。
和林派来的“慰问”使者,已经在路上了。他们会带来蒙哥的什么命令?会对金莲川幕府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忽必烈和他身边的贤才们,又该如何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没有人知道答案。
风还在吹,谷子还在“哗啦啦”地响,金莲川的阳光依旧灿烂。但忽必烈隐隐感觉到,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正在慢慢向他靠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