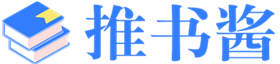献陵夜归后的第三日,早朝。
李世民端坐于龙椅之上,神情平静如水,但熟悉他的臣子们却能感觉到,那份平静之下,潜藏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威压。渭水之耻的阴霾,似乎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涤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真正属于开创者的、沉甸甸的自信。
“北境已定,然国不可一日无法。”他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太极殿的每一个角落,“朕闻,大理寺少卿戴胄,近日判了一桩棘手的案子。”
戴胄闻言,立刻出列,躬身道:“臣不敢。”
“淮南王李道宗的侄子,强占民田,逼死人命,可是实情?”李世民的目光,如同一把无形的尺,落在了戴胄身上。
此言一出,朝堂之上顿时响起一阵细微的骚动。李道宗是宗室亲王,战功赫赫,他的侄子,便是皇亲国戚。戴胄不过一介六品少卿,竟敢动他?
戴胄面不改色,朗声回道:“回陛下,人证物证俱在,罪无可逭。臣已依《唐律》斩立决。”
“斩了?”李世民的眉毛微微一挑,“李道宗可曾为你求情?”
“他曾亲至臣的府邸,愿以千金百亩换其侄一命,被臣严词拒绝。”戴胄的声音里没有丝毫犹豫,“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若因皇亲而枉法,则国法将不复存,陛下何以治天下?”
“好一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李世民猛地一拍龙椅扶手,站起身来。他走下御阶,一步步来到戴胄面前,满朝文武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戴胄,你知道吗?朝堂之上,有人骂你‘不近人情’,有人上书弹劾你‘攀附皇权,酷吏行径’。他们都说,你该杀。”
戴胄抬起头,直视着皇帝的眼睛,平静地说道:“臣不知。臣只知,臣手中捧的是大唐的律法,不是淮南王的金子。臣心中敬的是陛下的江山,不是权贵的颜面。若因此而死,臣死得其所。”
李世民凝视着他,足足有十息之久。然后,他突然笑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畅快的笑声。
“说得好!说得好啊!”他转身,面向群臣,声音陡然拔高,“朕今日就要告诉你们,朕要的,就是戴胄这样的‘不近人情’!”
“朕的律法,是刻在鼎上,昭告天下的!它不是一纸空文,不是用来约束百姓,却放任权贵的工具!朕要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在这大唐的土地上,没有谁能凌驾于国法之上!”
“朕的帝国,不是靠人情维系的乡里,而是靠法度支撑的巨厦!任何敢动摇这基石的人,无论他是谁,朕,和戴胄的大理寺,就是他的断头台!”
他当场宣布:“擢升戴胄为御史大夫,正三品,赐丹书铁券,除谋逆大罪,可赦其死罪三次!”
此令一出,满朝皆惊。这不仅仅是升官,更是皇帝用最直接的方式,向整个官僚体系宣告了他依法治国的决心,和对执法者无条件的保护。
处理完戴胄的事,李世民的目光又转向了房玄龄和杜如晦。
“玄龄,如晦,吏治是国之命脉。朕不要求你们个个都是圣人,但朕要求你们,必须为朕选拔出真正的贤才。对于那些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官吏,无论他地位多高,背景多深,一律严惩不贷!朕要的是一个清明、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
“臣,遵旨!”房玄龄和杜如晦心中激荡,齐声应诺。他们知道,一个真正属于“贞观”的时代,从今天起,才算真正拉开序幕。
最后,李世民的目光落在了魏徵身上。
“魏徵,朕知道,你最近一直在整理前朝的史书。”
“是的,陛下。臣正在编纂《隋书》。”
“很好。”李世民点了点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朕要你,不仅要写隋朝的灭亡,更要写清楚,它为何而亡。写它的君主是如何从明君变成昏君,它的朝政是如何从清明走向腐败。朕要让这本书,成为我大唐所有皇室子弟和朝臣的必读之物!朕要让他们时时刻刻都记住,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一刻,三位大臣都明白了皇帝的用心。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权力的巅峰之后,李世民没有沉溺于胜利的荣耀,而是以一种近乎偏执的清醒,开始为这个庞大的帝国,构建最底层的制度保障。
他要用严明的法律,来约束权力;用清明的吏治,来推行仁政;用历史的教训,来警醒未来。
退朝后,魏徵留了下来。
“陛下,今日在朝堂上,您展现的,是一位真正圣君的风范。”魏徵由衷地赞叹道。
李世民却摆了摆手,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熙熙攘攘的宫廷。
“魏徵,你知道吗?昨夜,朕去了献陵,问了大哥。”
魏徵心中一惊,没有作声。
“我问他,这一切,值得吗。”李世民的声音很轻,“今天,朕用行动回答了自己。”
“值得。”
“因为朕要建立的,是一个不再需要兄弟相残,就能顺利传承下去的帝国。是一个有法可依,有史可鉴,任何人都无法轻易撼动的帝国。或许,这便是对他,对四弟,对所有在这条路上牺牲的人,最好的交代。”
魏徵看着皇帝的背影,那个背影,在晨光中显得有些孤独,却又无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