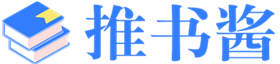第9章
开元寺中,禅房交锋
五店市的石板路上,午后的日头晒得人有些发懒。
王老五跟在林风身旁,用手背抹了把额上的汗,咂摸着嘴。
“我说无瑕啊,你小子这几天,真是邪了门了!”
“查起案子来,跟换了个人似的,脚不沾地啊。”
他顿了顿,又道:“我们这才刚从那瓷器铺出来,这就奔开元寺去?”
“我说,这五店市好歹也是个热闹地界,不寻摸个地方,填填肚子再走?”
林风的思绪还停留在李瑶最后那番话上。
开元寺,本悟法师。
李瑶说,安能敛财引发众怒,这位法师曾出面调解。
此人,或许是解开安能复杂关系网的又一个关键。
李无瑕的身体本能地渴望歇息,腹中也有些空空。
但林风的意志坚决。
“王哥,案子要紧。”
“先去开元寺。”
王老五瞧着他这副“油盐不进”的模样,只能无奈地撇撇嘴。
“还没到饭点。再说,公事为重。”林风抱胸往前走,没理他。
“这效率,啧啧,比老张头年轻那会儿,催命还催得紧!”王老五语气里带着明显的诧异,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敬佩。
林风没有回应王老五的打趣,他的思绪还停留在李瑶那双平静下燃烧着滔天恨意的眼睛,以及她提到的安能死前急切筹钱的举动。以及李瑶提到的开元寺主持本悟法师,说他曾出面调解过安能与信众的纠纷。
林风直觉,这或许是另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一个德高望重的僧人,一个声名狼藉的明教法师,他们之间的交集本身就耐人寻味,更何况是在那样激烈的矛盾之下。越是看似不相关的个体,在特定事件中产生的交集,往往越可能隐藏着关键信息。
两人朝着开元寺方向行去。
泉州作为南宋时期的国际大港,不仅商贸繁盛,宗教文化也兼容并蓄。开元寺便是这座城市佛教文化的象征之一,始建于唐朝,历经千年风雨,香火绵延不绝。它不仅是僧侣修行的清净之地,也是百姓祈福、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场所。寺庙的建筑风格古朴大气,飞檐斗拱,雕梁画栋,处处透露着历史的厚重感。
然而,对于李无瑕这具身体而言,前往这样庄严的场所,内心却升起一股莫名的敬畏与胆怯,手心不自觉地开始冒汗。
林风的意识努力压制着这股本能的畏缩,提醒自己此行的目的——揭开真相,无论它藏在多么神圣的外衣之下。任何外在的身份和环境,都可能成为掩盖真实动机的伪装。
还未进入寺门,便能感受到一股宁静祥和的气息扑面而来。
寺门口人来人往,香客络绎不绝,有虔诚跪拜的老者,也有好奇张望的孩童。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檀香味,夹杂着寺内花草的清香,让人心神不由得一静。
但寺庙并非全然的静谧。
正如王老五所说,浴佛节临近,寺内一片忙碌。年轻的僧侣们在清扫庭院,居士们在擦拭佛像,准备供品的香气从斋堂飘来,显得有些嘈杂,却也带着一种生机勃勃的烟火气。
在知客僧的引导下,林风和王老五穿过庄严的殿宇,来到本悟法师的禅房。
禅房布置简单素雅,窗明几净,一方案几,几只蒲团,再无他物。
本悟法师坐在蒲团上,正在翻阅一本厚重的经书。他约莫五十来岁,面容慈祥,双眉低垂,眼中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宁静与智慧。
见到两位捕快前来,他缓缓起身,双手合十行礼,语气温和,带着一丝看破红尘的淡泊:“两位官爷远道而来,可是有何事?”
林风定了定神,努力克服身体的紧张,用一种尽量不失礼数但也不卑不亢的语气说明了来意:“法师,我们是泉州衙门的捕快,前来向您打听一些关于安能法师的事情。听说前些日子,您曾出面调解过他与信众的纠纷?”
本悟法师闻言,平静的眼底深处掠过一丝极细微的波澜,瞳孔似乎有瞬间的收缩,如同平静湖面投入一颗小石子,但这丝涟漪迅速消失,快得仿佛只是林风的错觉。
林风暗自记下这一点,一个人的名字,能让一位高僧出现如此细微却真实的生理反应,这本身就说明了一些问题。
对于一个与安能交集不深的人来说,这个名字似乎在他心中激起了超出预期的反应。
他请两人坐下,叹了口气,说道:“阿弥陀佛。确有此事。那位安能法师……哎,贫僧本不愿多言他人是非,只是他近期的行事,确实引发了不少非议,连寺外都有不少信众前来求助,贫僧这才不得不出面。”
接着,本悟法师轻捻佛珠,面容平静地开口,仿佛在谈论一位熟识的老朋友,语气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
“说起来,那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许多信众都跑到寺外,情绪激动,说是被安能法师给蒙骗了血汗钱。”
他顿了顿,目光投向窗外那棵枝繁叶茂的古老榕树,树影斑驳地落在禅房的地板上。
“说来也是为了钱财二字。安能法师近来传教,手段与旁人不同。他呀,总喜欢故弄玄虚,大肆宣扬什么‘末日近在眼前’,‘泉州将有大灾祸’,还说什么这是‘明尊’降下的旨意,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可偏偏就有人信他那一套,还真以为捐了钱就能‘赎罪’,‘消灾避祸’,保得家人平安,甚至能在‘末日’之后进入‘真神’的国度,享永世的福报。他那口才,也是了得,说得绘声绘色,把许多百姓吓得人心惶惶,生怕真有什么灾祸降临,纷纷拿出家中积蓄,甚至变卖家产,只求能得个心安,换取那虚无缥缈的‘平安符’和‘入国门票’。”
本悟法师说到这里,语气中带着一丝明显的不认可之意,仿佛在谈论一位熟识,却又颇为不屑的老朋友。
他仿佛亲眼见过安能传教的场景,对安能的伎俩了如指掌。这种熟悉感,与他自称的“不得不出面”调解的被动角色,以及后来声称的“点头之交”,形成了明显的矛盾点。
林风知道,人们在回忆和描述时,对细节的掌握程度往往与其对事件的参与度和对相关人物的熟悉度成正比。一个仅仅是“出面调解”的局外人,很难有如此生动且带有个人评判的描述。何况还是一个看起来早已超脱俗世、遁入空门的僧人。
“捐钱赎罪?消灾避祸?”王老五听得直皱眉头,忍不住插嘴道,“这不就是骗钱吗!打着神明的旗号,干些坑蒙拐骗的勾当!”
“正是如此。”本悟法师点头,脸上露出深深的无奈,“信众们起初是信的,毕竟谁不盼着平安顺遂呢?可日子久了,他们发现那些捐出去的钱,并没有像安能法师宣传的那样,用于救济穷苦,或是修缮明教的聚会场所。反倒是有传言说,安能法师自己住着豪宅,吃香喝辣,穿着绫罗绸缎,挥金如土,过着比那些富商大户还要奢靡的生活。”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仿佛对安能的做派十分熟悉,甚至能想象出安能骄奢淫逸的样子,“他甚至购置了不少奇珍异宝,据说都是价值连城的物件,对外宣称是‘供奉真神’,实则据传都是入了私囊。”
林风心中一凛,“奇珍异宝”、“价值连城”……这是否就是李瑶提及的安能急切想要购买的东西?等等,奇珍异宝?是否也包括那颗他穿越前在博物馆见过的宝石?
他强压下心中的波澜,追问道:“传言说是他自己挥霍?可有实证?”
“传言毕竟是传言,贫僧与安能法师只是点头之交,并未深交,这些事情,贫僧也只是耳闻,并未亲眼所见,不好妄下定论。”
本悟法师回答得很快,仿佛在刻意撇清自己与安能的关系,但他的眼神却闪过一丝了然,仿佛对这些传言心知肚明,只是不愿多说。
林风注意到,本悟在说“点头之交”时,视线有短暂的游移,避开了与林风的直接眼神接触,这在说谎或试图掩饰的时候很常见,因为维持眼神接触的同时编造谎言会增加心理负担。
本悟继续道:“只是信众们觉得,他们省吃俭用,甚至倾家荡产捐出的血汗钱,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了,心中自然愤懑不平,认为自己被玩弄了。他们觉得安能法师违背了他们所信仰的教义,是彻彻底底的欺骗。矛盾越发尖锐,从口角争执发展到肢体冲突,眼看着就要酿成更大的祸事。”
本悟说到这里,轻叹一声:“有几位受骗较深的信众,眼见官府一时没有作为,又怕事情继续发酵,便找到了寺里,恳请贫僧出面。他们知道贫僧在泉州薄有名声,也素来主张化解纷争,希望贫僧能从中调解,让安能法师归还钱财,或者至少给个说法,平息众怒。”
他顿了顿,双手合十,脸上再次恢复了那种悲天悯人的神情:“贫僧感念他们受苦,不忍见矛盾扩大,更怕无辜百姓因此受到伤害,这才答应出面,希望能化解这场纠纷,劝安能法师回头是岸。”
本悟法师的讲述详细而流畅,他对安能敛财手段的描述,对信众心理的揣摩,以及对整个事件经过的把握,都显得异常精准。
林风在心里默默分析着:本悟说话的时候,语调虽然平稳,但提到安能的某些行为时,比如“故弄玄虚”、“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他的嘴角会不自觉地向下撇,眉宇间也会闪过一丝厌恶。
这些都是非常细微的表情,普通人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但在林风看来,这就像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激起了隐藏在深处的真实情绪。
一个只是“点头之交”的人,很难对另一个人的行为细节、甚至敛财手段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和如此鲜明的情感反应。这更像是在评价一个自己非常熟悉,并且打心底里瞧不上的人。
这种情感的流露与他声称的“点头之交”再次形成矛盾,这种言语内容和非言语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是判断对方是否诚实的重要信号。
林风决定进行试探。他想看看,当自己提及一些安能更私密的习惯时,本悟会有什么反应。这就像在审问时,拋出一个对方以为你不知道的细节,观察他的反应,以此判断他是否知情。
“法师,”林风清了清嗓子,努力克服身体的紧张,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一些,但李无瑕的身体还是让他感到喉咙发紧,声线有些发虚,“我听说,安能法师平日传教时,除了常说‘此乃真神旨意’,还有些特别的习惯,比如……他说话时,习惯性地会用手捻动衣角,或者在思考时,会不自觉地用指节轻叩桌面,不知法师可曾留意?”他说出这些细节时,眼睛紧紧盯着本悟法师的脸,观察着他每一个最细微的变化。林风知道,人在紧张或试图掩饰的时候,身体往往比嘴巴更诚实。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属于个体的习惯性行为,知情者在听到这些细节时,其反应会与不知情者截然不同。
当林风说出“捻动衣角”和“轻叩桌面”这两个细节时,本悟法师的眼神瞬间发生了变化。那是一种极为短暂的、几乎难以捕捉的慌乱,仿佛平静的湖面突然被一阵疾风吹过,荡起了层层涟漪。
他放在膝上的手,原本平静地捻动着佛珠,此刻却不自觉地微微一僵,指尖仿佛在轻微地抽动了一下,捻珠的动作也出现了不自然的停顿。
他原本慈祥的眼神,在那一刹那闪过一丝警惕和不自然,瞳孔再次出现轻微但可辨的收缩,这是典型的应激反应的生理表现。
虽然很快就被他强大的自制力掩饰了过去,恢复了平静,但他捻佛珠的速度,却似乎不经意间加快了那么一点点,这在行为分析中常被视为一种“安抚行为”,用以缓解内心的焦虑。
这些细小的动作,都是一个人在面对超出预期的信息刺激时,内心波动的外在体现。
“阿弥陀佛……贫僧与安能法师只是点头之交,他传教时的细节,贫僧并未留意。”本悟法师回答得很快,快得有些刻意,仿佛急于否认。
但他的眼神却闪过一丝了然,仿佛对这些习惯并不陌生,只是不愿承认。
他回答滴水不漏,却反而加深了林风的怀疑。一个仅仅见过几次面的调解对象,怎么可能让一位德高望重的僧人在听到这些细节时,露出如此明显的破绽?
这种极力否认却又无法完全掩饰的反应,恰恰说明他对这些细节非常熟悉,甚至可能亲眼见过安能的这些习惯,而且这些习惯勾起了他某些不愿触及的记忆。
林风判断,这种否认伴随着生理上的紧张反应,是典型的“说谎者信号”——试图通过迅速而坚决的否认来终止可能暴露真相的话题。
王老五在一旁听着,完全没有察觉到本悟的异常,他只是觉得李无瑕今天问的问题有些奇怪,怎么关注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了。他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林风,示意他别再问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但林风的内心却掀起了惊涛骇浪。本悟法师的反应,绝不是一个对安能一无所知的人应有的表现。他显然对安能有着某种不寻常的了解,甚至可能是非常熟悉的了解。而这种了解,是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
“法师,”林风没有理会王老五的示意,继续问道,声音虽然带着李无瑕固有的怯懦,但语气却异常坚定,“安能法师在泉州传教多久了?您是否知道,他来泉州之前,是何身份?与何人来往?”
本悟法师的脸色微不可察地变了变,他放在膝上的手再次紧绷起来,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泛白。他抬眼看了看林风,眼神中带着一丝探究和警惕。
林风知道,他成功地引起了本悟的注意和警觉,对方正在评估他的意图和所掌握的信息。
“安能法师来泉州已有两年多吧……至于他来泉州之前的身份,贫僧并不知晓。”本悟法师回答道,语气虽然平静,但林风敏锐地捕捉到,他的回答有些迟疑,且在说到“来泉州之前”时,他的眼神再次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并伴有轻微的吞咽动作,这可能表明他在有意识地筛选或隐瞒某些信息。
林风没有再追问,他知道,再问下去,本悟法师也不会透露更多。
但他已经得到了最重要的信息:本悟法师,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元寺主持,与死者安能之间,绝非仅仅是调解者与被调解者那么简单。他们之间,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秘密,一个足以让本悟法师在佛门净地也无法完全掩饰的秘密。
而这个秘密,或许就藏在本悟法师那段无人知晓的、来泉州之前的经历里。本悟为何要隐瞒这段过去?这段过去与安能的死又有什么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