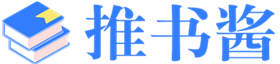风从河心吹来,穿过城南棚户与破院,带着一股潮冷的腥。日头一出,腥气便薄一层;到了傍晚,又像从砖缝里渗回去,把墙脚轻轻一舔。
姜梨与凉生在城南巷尾寻得一处破院。院门是用两扇不对称的门板拼起来的,门闩是根铁丝,弯了两道,扣上,再在外头压一块旧青砖。院里生着两棵槐,槐影瘦,叶子在风里哗啦。最里头一间屋还算干,墙角裂,梁上横着两道焦痕,像哪年哪月曾经走过火。
她第一日只做了三件事:补屋顶、清院角、找水。凉生上了屋,把芦苇片一片片压在裂缝上,用绳头纵横捆;她在下头接,递,剪,打结,手里永远稳。补完,凉生握拳,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可睡。
她点:勉强。
找水是第二件事。院里有一口破水缸,缸肚上裂一长线,像一条睡着的蛇。她蹲下看,指腹沿着裂处慢慢摸过去,摸到有一指宽的空。缸底还有半缸雨水,水面浮着几片槐叶。她把叶捞出,舀一勺,闻,有一丝陈味。她仰头看天空的云,云低,风东。她说:“先用来洗手。”
凉生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沥。
他搬出一只破篮,把屋檐下沥下的雨,一缕缕引入缸里。一会儿,缸面有了浅浅的涟。他眼里光淡,手上不急。他做每件事,都像在河水底搬一块石——知道轻重,晓得顺逆。
第三件事,是在院门上钉一条细细的红绳。红绳不显眼,只有在门半掩时,能看见一点点颜色。绳上结了三个小结——短、短、长。那是她与阿福约好的应答。谁若在门外吹那样的哨,她便在绳上轻轻摘下一结,挂在门内的栅上,算一句“来”。
红绳挂好,风把它吹得轻轻摆。她看了一眼,笑,把袖子抖一抖,袖里栀子的香淡淡浮起,又很快散。
立足之计,得先有个名头。她不敢打“医”字。医字太重,太招眼。她把一块破木板磨平,写了四个字:“补漏修缸”。木板竖在门内,从外头看,只能看见一边的“补漏”二字。她又把药箱藏在案下,案上摆一只破缸口,缸口边放着一团麻,一把细锤,一支旧刷。
桑二来看了一眼,笑,笑里有夸:“好名头。”
她笑:“借你的行当,背你的名头。”
桑二摆手:“你背不坏。往后谁问你,我就说你是我外甥女。咱城南,亲戚能多两家的总是好事。”
凉生在一旁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谢。
第一日有人来,是隔壁巷的一家。男人挽着袖,裤腿卷到膝,腿毛上粘着泥。他探头往院里看见“补漏”二字,便压低声音:“娘子,会补灶台吗?灶台里漏烟,眼睛熏得睁不开。”
姜梨点:“会。”
她背着小包去看。灶台裂在火眼旁,裂得细,细到常人看不出。她拿细粉与湿泥调和,夹上一点灰,摊在裂处。又把灶台下头的风口稍稍垫高,换了角度。男人看她抹泥,稳,心也稳了,便问:“娘子,会看人病吗?”
她抬眼看一眼他眼里的红丝,笑:“补灶也得看火候。”
男人嘿嘿笑,没再问。
第二日,有两个妇人来,请她去看“漏风”的窗。窗子是竹格,破得不像样。她看了看,先替她们把窗一格一格绑紧,用细布缠在竹格上,挡风。临走,她递过去一包自晒的艾绒:“夜里熏一熏,别直对风口。”
妇人接过,眼里一亮:“这东西,桑二也给过,说能去湿。娘子手里这包,香。”
她笑:“栀子混了艾。闻着才不呛。”
如此三日,破院门口来往渐多。有人真来补漏,有人来借一碗热水,有人来打听脚夫的事,有人来送一把玉米穗。阿福也来,手里拎一只空木箱,箱里塞了三根破竹竿。他在门口“吱”一声,把箱一放,眼睛滴溜溜看一圈:“娘子,凉哥。”
凉生抬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近。
阿福压低声音:“昨夜黑边小帽的人又转了一圈,问谁认得‘修缸的娘子’。我说不认。我把他带去看了另一家修鞋的。他半信半疑,没盯上。”
姜梨点:辛苦。
阿福咧嘴笑:“不累。”他伸手从袖里摸出一小包,“给你。宫市头一拨‘牙’在点人。点的是能下水的、能上梁的、会看字的。会看字的价比上回高。”
她接过,包里是一张用炭磨过的薄纸,纸上列着几处集口与时辰。她在薄本上记了四个字:“禁军过巷”。
是在这一天的傍晚,邻巷传来哭。哭声不大,却直直往人心里钻。哭的是个小孩,声音细,像猫在角落里叫。哭声里夹着一个老人的喘,喘得乱。有人在门口探头,叹气,叹完走;有人走了两步又停,又走。
阿福最先跑去,转头便带了两步回来:“娘子,祖孙俩。老的喘,小的烧,没人敢进。”
凉生看一眼姜梨,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去。
邻巷尽头是一间更破的屋,门槛烂,门口的草帘裂两道,垂着。屋里一股湿冷的霉,墙上糊的旧纸起了毛。角落里躺着一个老妪,头发雪白,脸瘦得只剩骨,喉间的喘粗而急。炕上一团被子里缩着一个小孩,额头热得烫手,眼皮红,嘴唇干,开开合合地出气。
屋里没有水,只有一只粗碗,碗底凝着一层凉油。阿福把袖子一卷,去院里找水。凉生转身出去,三步并两步回,手里端了半盆温水,是他刚才把缸里头那点太阳水烫一烫,用布包着端来的。
姜梨先看老妪。老妪背脊因为久卧而塌,她让凉生扶着老妪坐起,用枕垫住背。她把手轻按在老妪胸口,听了一会儿气,问:“几日了?”
门口有个男人探头,面相粗,手长,衣襟上有灰。他嗫嚅:“三日。前日还有口气,昨夜里忽然紧。小的也烧,烧了一天一夜。我们去叫衙门口的当差,他们说先交钱,没钱不管;去找庙里的香火婆,又说最近不收病人。咱这院……唉。”
姜梨“嗯”了一声,伸手把老妪的袖子拉高,看到了青筋浮起的手臂,腕脉细而乱。她取出砭石,先在火上稍热,再在老妪胸前穴道间轻轻一划一停,划的是气路,停的是喘点。她又让阿福把窗开一指宽,“只一指,不许多。风太直,会伤。”
老妪的喘在半盏茶后慢了一些,像被人从水里托了一把。她翻看老妪的舌,舌边泛红,苔黄。她低声:“热郁。晚间用温水擦身,勿用冷。”
转而看小孩。小孩的额头发烫,眼珠在眼窝里转两下又歇。她摸后颈,汗出但不畅,手心湿。她问:“吐泻没有?”
男人摇头:“不吐。昨天还吃了半个窝头,夜里吐出来一点点,都是水。”
“哭闹?”
“他不哭。就是这样喘着睡,一醒就要水。”
她点。她拿出随身的小药包,捻出一点白色的粉,蘸了水,抹在孩子的唇皮上,再用温水一点点从口边喂进去。她把炕头的被子掀开一角,让热气蒸出来一些,又用艾绒在炕脚轻熏,让汗从脚底下透一透。她对男人道:“找半碗稀粥来,不要太稠,不要高油。”
男人“好,好”地应,转身去借。阿福把门口挡了一下:“我去快些。”他脚下快,两步没影。
凉生站在屋角,背对着人群,手在袖里。有人从门外探头,他侧身一挡,挡住了屋里的光。他的影像一堵稳墙。
老妪的手忽然摸摸摸,摸到了姜梨的袖。她声音细得像风丝:“姑娘,你是哪个庙里来的仙?”
姜梨笑:“补缸的。”
老妪眼里光动了一下,像是笑了一下。笑还没落下,喘又一紧。姜梨把她的手按回被里,低声:“你只管听气。气长,命就长。”
粥来了。是阿福端的,粥很稀,飘着三粒米。姜梨接了,先晾,吹。她把小孩抱起来,托住后脑,极慢极慢地喂。小孩的喉间一开始像要拒,后来吞下去一点,喉结轻轻动了一下。她等一等,再喂一点。三次以后,小孩的额头上出了细细的一层汗,汗珠挤在发际。
她把手按在孩子的掌心,掌心湿,指端冷。她用手背测了一下孩子的鼻息,略和缓。她把孩子放回炕上,用湿布敷额,把布换了两次。她对男人道:“夜里要有人守着,四更换布,五更喂水。孩子睡着也要喂一点。”
男人点头如捣蒜:“守,守。”他手大笨,却突然红了眼。
屋外,脚步声渐多。邻巷的人围在门口,又不敢进。有个老妇人低声嘀咕:“这娘子手稳。昨儿她把咱家灶台一抹,今儿火就不直冲了。”另有一个男人说:“她门口写的是补漏修缸,怎么会看病?”有人回:“桑二说是亲戚。”
阿福探头看一圈,冲门外的人使了个眼色:“散散,别都挤门口。禁军要过巷,别让人看见一屋人。”
人群像水一样散了一层,又在远一点的地方化开,仍旧看。
夜深。老妪的喘慢了下去,像一口气终于在胸里安顿了。孩子的热退了一分,额头的汗干湿交替。姜梨把最后一缕艾捻灭,用钝刀背在穴位轻轻敲了三下。她收手时,手心也出了一层薄汗。她抬头,凉生目光与她一对。他的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稳。
她回以一压:稳。
出屋时,男人跪下,膝盖“咚”地在地上磕了一声:“娘子,救我们祖孙一命。我们家没钱。只有两根木头、半袋麦糠、一只旧瓢,你看要哪个?”
凉生上前,把人扶起。姜梨笑:“你明日替我把院里那口水缸挪一挪,架高半寸。我不要你的瓢。”
男人愣了一瞬,连连点头:“好,好。”
她又对门外看着的人道:“今晚禁军要过巷,谁家门口有三点一划的记号,先拿水泼开,再拿灰糊。明天早上再擦,不要留下痕。”
人群里有人倒吸一口气:“你也知道那个记号?”
姜梨没答,只抬手把门帘放下,堵住风。
回到破院时,夜风正好。风铃“叮”一声又一声,像谁用指尖轻轻拨。凉生卸下肩上背的水,往缸里加。缸里的水像把影子养了一夜,黑里有一点亮。姜梨把药箱拉出来,将用过的砭石、镊、针一一擦净,放回布袋。她手指有些抖,便把手按在膝上,慢慢停住。
“你累。”凉生不出声,用手说。掌心向下,轻轻一压。
她笑:累,也稳。
第二日一早,老妪的喘更缓,孩子的热退了大半,眼睫毛上挂了一粒小汗珠,像露。男人按约来,把水缸搬高了半寸。凉生在缸下垫了两块砖,把缸口朝里,避风。男人抬头看了一眼他剥开的袖,臂肌上的力线清楚,便悄悄咽了一口唾沫:这位不说话的人,力气大。
这件事过后,巷里便在口口相传。有妇人来敲门,抱着孩子,孩子眼屎多,咳,夜里咳到吐。她给抓了点桑叶与杏仁,熬水,教怎么捏鼻喂;有老人来,说腰疼,她只给了一袋温盐,教他夜里热敷;有人手背起了红疹,她让他先停用井边的洗衣草,用清水煮一煮再洗。
她不收钱,或者只收一点点——有人送两把菜,有人送一小只木梳,有人送一把旧钳子。她把木梳给了阿福:“你头发该梳。”阿福笑:“我头发不配这梳子。”她把钳子给了凉生。凉生把钳子放在案角,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用。
名声就这样轻轻起了。不是大张旗鼓,只是口口相传,像风把一枝花的香吹进另一枝。有人在南市的大茶棚背后说:“城南有个补缸娘子,能看喘救热。”有人在脚夫的院里说:“她手稳。”有人说:“她袖口有栀子香。”
名声起,眼睛也随之起。午后有两个穿着整齐的人站在巷口,装作聊天,眼却不看人,只看门。阿福从破墙上翻过来,一屁股坐到院里:“娘子,黑边小帽那一路,没再见。倒是来了两个新脸,鞋上灰细,滴水点没有,不像走河滩的人。”
姜梨嗯了一声,低头把门内的木牌翻了个面,把“修缸”字遮在里头,只露“补漏”。她把细锤放回案下,又把药箱再往里推一个指。
凉生在门边站着,像一截影。他目光只往三处:巷口、屋脊、对面那棵槐。他的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来。
是“市牙”。打头的是一个四十出头的人,脸白,手指修得圆,衣襟内侧绣了细细的边。他走到门前,先看木牌,再看院。看完,笑了一下:“娘子生意好?”
姜梨点:“补漏,补得过来。”
那人“啊”了一声,像没听见“补漏”,只顺着自己的意思说:“我们是市里做事的,替人找东西。听说娘子手稳,认得老物,敢不敢去宫市坐一日?”
她摇头:“我手只认裂缝,不认老物。”
那人的笑没有下来:“娘子不试试?今日价高。”
她还是摇头,笑着:“不识。”
那人也不恼,目光落在她袖口停了一瞬,像闻到了那一缕淡栀子。随即他把目光挪开,朝院里往里看,像要看案下。凉生在一旁不动,只在那人目光要越过案沿的那一瞬,向前走了半步。他肩胛轻轻一侧,像一块石头挡住了一条水。
那人笑不见了半分:“这位是?”
“补缸的。”她答。
那人“哦”了一声,像也不愿把脸笑僵,拱了拱手,转身走。走到门口,他忽然回头,看了一眼门上那条细红绳,嘴角轻轻一动,像是记了什么。又走。
“他记了绳。”阿福从墙头翻下,声音压得极低,“他要回来。”
姜梨把红绳收起,换上一条灰线,灰线结成两个结——短、长。她在内侧的栅上也换了一条,依旧三结,只把位置往里移一寸,不容易被外人见。
这日夜里,风换了向。北风裹在屋檐,吹得墙角的灰一阵阵落。凉生在院里练手,指间两根竹签如鱼,起落无声。他停下时,手心微微出汗。姜梨递给他一块布。两人并肩在门槛上坐了一会儿,听河水声。“你手,”她轻轻说,“有一瞬乱。”
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歉。
她笑,摇头:“不必。”她看他手背,手背的筋像活线,安静时却像一块温石。她伸手,把他的指按在自己的掌心里,压了一下:稳。
次晨,门口来了两个禁军。甲叶重,靴上有泥。他们只是走在巷里,左看右看,在门框下按了一下,指尖蘸了一点灰,在墙脚轻轻划了一道。三点一划。划完,其中一个忽然抬头,看到了门内的灰线结。他眼神没有多挪,只在那一瞬略停,便走。
阿福从对面槐树后钻出来,跑得无声。他一口气没喘:“娘子,今夜他们要过巷。宫市开前一晚必过巷,这是规矩。你们要不躲,就要借影子。”
“借影子?”她问。
“借脚夫的影子。今晚脚夫要走一拨货,你们若跟在他们货后头走,从‘影子’里过去,就不算人。”
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可。
午后,又有两件事。第一件,是那祖孙又来。老妪能下炕了,孩子能自己走两步。老妪提了一个用旧布包起来的小包,递给姜梨:“姑娘,这个,是他爷爷留下的。不是好物,是旧布头。我想,姑娘手巧,能用得上。”
她接过,打开,是几小片做衣裳时裁剩的碎布,有细麻,有粗布,有一小条荆布,摸上去滑且韧。她笑:“正好,补缝。”
第二件,是脚夫的老头来,把“借肩牌”又递回来:“你前日借给那小崽子的牌,我认得。他还回来时说‘娘子叫还’。我今天给你一张新的,押的是我的印。你要走货路,用这个更稳。”
她接下,郑重:“借你名头,算我欠。”
老头笑:“欠,慢慢还。只别坏我的名。”
临近黄昏,南市的大茶棚人声渐稀。有人在背后墙角画了两笔,画得极轻。阿福蹲下去看,说:“不是我们的记号。是‘叶’的。”
“半羽?”
“嗯。”阿福伸手从墙角掏出一片薄薄的纸叶子,叶上压了半边羽的影。他压低声,“他们盯着你了。”
凉生目光沉,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换。
姜梨点:换。
换什么?换门,换路,换名头。
晚饭后,她把门内的木牌彻底收起,案上摆的旧缸口也搬了个位,换成一只破竹筛,筛里放了一团已经拧干的粗布,像是“晒”。她把院门的闩改了一个扣,扣从外拉改为内推,又在门后挪了一只破凳,挡道。她把真半玉换了位置,缝在衣内夹层下沿,靠近腰处。假半玉则放在靠门的一只空竹筒里,任人一翻便见。
她给阿福布置:“今晚你不跟。你去桑二那边待着。有人找你,就说你腿伤,跑不动。”
阿福被她按着肩,心有不甘,眼却亮:“我知道。短、短、长,我会吹。”
卯时初过,脚夫的院里传来一阵低低的号子。十几个人肩挑背驮,从巷口出来,货盖着油布,走得稳,不急不徐。姜梨与凉生在尾后两步,跟着影子走。影子把人吃进又吐出,像河水把小鱼裹进去再放出来。巷口的禁军看的是货,不是人。脚夫老头远远看了她一眼,像是在说:“不要乱动。”
过巷之后,他们绕到城外小道,沿河行。河边一排排芦苇,风吹过去像一阵细雨。走到一处破桥下,脚夫歇脚。老头把烟袋点上,吸一口,朝地上吐一口烟雾,压尘。他侧着脸问:“娘子要把名头扔了不?”
她笑:“换个更破的。”
老头笑得肩膀抖:“你这人,怪。”
回到院时,夜过半。门上不知何时多了一道极浅的划痕,痕在门闩旁,像是指尖轻轻一触。她伸手去摸,手心里有一丝粉。她把粉抹在舌尖,苦,像某种草药的末——冰片混了点别的。她脸色不动,把门闩轻轻一推,门开。
门后无物。院里风平,槐影落一地碎叶。
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盯。
她点:盯。
第二天起,来求诊的人更多了。有的是被风吹到背疼的脚夫,有的是被河水泡烂脚趾的搬运,有的是哭到声嘶的妇人。她一一看,一一说,收的不是钱,而是“事”:有人帮她把院里的墙缝糊一糊,有人帮她把屋檐下的风漏补一补,有人帮她去河边挑一担清水。她把谁帮了的“事”记在薄本上一页,写:“某日,某人,某事,某谢。”
这页翻到第三行时,发生了另一件事。
午后,一个穿灰青短襟的年轻人来,眼下有青,目光游。他自称是东市“广惠堂”的伙计,说掌柜想请她去看看一位“客”的病,重,银子好说。她笑着摇头:“我只在这儿补漏。”他又笑,说:“补漏也行,漏的是人的气。”她没应,他笑容便淡了淡,拱手走。
阿福悄悄跟了一程,看见那人路过一处墙角时,低头用鞋跟在地上蹭了一下,蹭出一个极浅的点。他忍着没上去,只回头吹了三声哨,短、短、长。
姜梨把薄本翻到“识敌”那一页,添了两字:“新牙”。
傍晚,祖孙俩又来。老妪带着孩子,孩子手里握着一只小石头,是从河边捡的。孩子把石头递给凉生:“给你。”凉生伸手接,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谢。孩子学着他,把手掌也压了一下,咯咯笑。老妪眼里蓄了一泡泪:“姑娘,我不识字,给不了你别的。你救了我们命。我家老头子在世时,常说‘世上有恩,不要忘’。我记。”
姜梨把一只小布袋递给她:“里头是几片艾绒与两片桑叶。夜里让孩子泡泡脚,别太烫。你的背上,我给你按两下,你记住哪里热,就拿温盐敷哪里。”
名声就这样像火星落在干草上,先有一小点亮,然后一线线带开去。到了第三天,巷口有人远远地喊:“姜娘子在不在?”喊完又压低声:“补漏的在不在?”
她人还没出门,凉生已经站到了门边。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慎。
是禁军里一位年纪不大的小军官,腰直,眼锋利,却不凶。他身后跟着两个兵。他敛了敛身形,向院里看,声音放得很小:“有人在巷口说你能救喘。我娘……”他说到这里,喉间动了一下,像卡了一口气,“我娘昨夜喘得不行。内城的郎中我也请了,说年纪大,心虚,开了两贴安神。我想,来试试。”
院里静了一瞬。阿福的眼睛在凉生与姜梨的脸之间转。桑二不知什么时候也到了门口,站在远一点的槐树阴里,眼里有担忧,也有一丝奇怪的光。
姜梨说:“我只补漏。”
小军官看着她,忽然低头,拱手:“求你。”
她沉默了一息,点头:“去看。”
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险。
她回以一压:须。
入内城要凭帖。小军官取来一张便条,字写得利。城门口兵士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姜梨与凉生,放行。城里与城外像两层不同的天。街道整,砖不崩,风里没有腥。她垂着目,不看牌楼,不看雕梁,只看脚下的影子。
小军官的家不大,却干净。屋内有一股安神香,香太重,像有一层雾。床上老夫人面色白,唇青,脉弱而浮。她先让人把香撤了,又把窗开一指。她用砭石在老夫人背心轻点,点过之后,老夫人胸口一合一张,喘稍稳。她让人用温水擦手,擦脚,揉掌心,揉到掌心热为止。她不开药,只写了四条:“撤香,开窗一指;晚间温水擦身;枕头垫高半寸;夜里勿惊。”
小军官看她只写四条,神里一紧,像怕她是个骗子。她笑:“明日再看,不好,再药。”
出门时,小军官塞给她一锭银。她不接,摇头。小军官硬塞。凉生伸手挡了一下,掌心向下,轻轻一压:不。
小军官低声:“让我心安。”
她看了他一眼,接下,随手又塞给了站在门外的一个看门小厮:“买两斤干草,晚上用来熏脚。”小厮愣了一下,红了眼。
回巷口时,天已黑。门口有人等。是那位“市牙”的远亲。他笑容仍旧稳:“娘子,今日去了内城,见了官家的人气,心里该也有底了。宫市的事,不躲得过的。”
她也笑:“躲一下,喘一喘。”
他笑意更深:“娘子真会说话。那我给你指一条路。明夜禁军过巷以后,后夜三更,有一处‘叶’会在河心摆一盏小灯。你若把要卖的旧物放在灯下,明日便有人来取,银放在灯边。无主之物,皆归宫市。娘子若有旧物,不若早了。”
她看着他,目光淡,笑意淡:“你们摆灯,也怕风。”
他一怔,笑意里忽然多了一丝寒:“娘子说笑了。”
他走后,阿福凑近:“他嘴角有个小疤,是被什么划过的。手指甲修得圆,鞋跟有一点泥,是河滩细泥。”
姜梨在薄本上添字:“灯,河心。”又写:“风。”
名声起,关注来。来问的,来探的,来盯的,像三股水从三条缝里挤进来。她把每一股水的方向记下,用砖头堵,用草塞,用绳系。她在院门里挂上了一只破竹筛,筛上搭了一块灰布。灰布上缝了两针粗线,像是补。有人问,她就指灰布,说:“今日只补,不看。”有人求急,她便在灰布上再添一针,表示“稍等”。
桑二看她这些小法,笑骂:“你这是在城南立规矩。立规矩的人,要担。”
她笑:“担,但稳。”
第四日清晨,内城的小军官派人来报,说老夫人夜里好睡了一刻,喘减。她心里一松。午后,那位小军官竟亲自来,站在门外,没进,只远远一揖:“谢。”
这一揖,像石子入水。巷里的人便知道“补缸娘子”的手连内城都用了。有好意的,便更好;有坏意的,便更坏。
黄昏,河沿起雾,城南像被一块湿帘罩住。阿福从雾里钻来,鼻尖冷,眼睛亮:“娘子,今晚的‘灯’,我看了。河心中,有一盏。风北,会偏。”
她点,摸了摸他发梢上的水。凉生站在门影里,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试?
她摇头:不。
她低声:“我们不把东西放在灯下。我们把别人的东西,从灯下拿走。”
阿福“哎呀”一声,随即又压低声音,笑得像猫:“我知道了。”
夜半,他们沿河行。河心的灯如约在,灯下有一个小小的油纸包。雾重,灯影被风吹得歪,像随时要灭。凉生下到浅水,脚下踩得稳,手伸出去,像从一条蛇的舌头旁边把一粒米捏走。他把油纸包拿起,轻轻一看,是一枚半羽银叶与一张纸。纸上写着两行小字:“银在草堆里;物在你手里。”
她笑,把纸折成极小的一条,夹进薄本。她把银叶交给阿福:“你去把这叶子丢到黑边小帽常走的巷口。”
阿福“唰”地去了,像影。
他们顺着河边又走了一段。雾里有人影一晃,又一晃。有人在灯下伸手,摸了个空,便骂,骂声又被雾吞了。
回院时,门上灰线结已经被人动过。不是大动,只是往右移了一指。她伸手把它原样挪回,心里像有一只细小的鱼,尾巴轻轻拍了一下。
第五日午后,禁军过巷。三点一划,画在许多家的门前。她这扇门前,却空着。不是他们看漏,而是脚夫的影子把她遮了。她站在门内,看他们画,看他们走。她看见队尾有一双眼睛,年轻,却冷。那双眼睛在她门上略停,又在她的袖口略停,最后在她的手上一停。
凉生掌心向下,轻轻一压:记。
她点:记。
傍晚时分,城南的风忽然急。院外有人敲门,敲得“笃笃”,不快不慢。阿福先吹了三声哨,短、短、长。她回以门内轻轻两下敲,短、长。帘一掀,是桑二。他进门,第一句话:“今夜,别睡。”
“宫市要开了?”
“今夜过巷之后,当夜市牙就去敲门。”桑二压低声,“他们要敲有记号的门,也敲没有记号、却有人气的门。你这门,人气足。”
她笑:“人气,能遮。”
桑二也笑,苦笑:“你遮得住风,遮得住‘叶’吗?”
她不答,把灯捻灭,又捻亮。她在灯下把薄本翻到最前一页,写了一行字:“暂居城南。立足之计:借名、借路、借影。今日起,名轻,路暗,影多。”
夜深,风更急。巷口起了脚步声,散,又聚,又散。门外有人影掠过,有人指着墙脚,又移开。远处的河里,灯忽明忽暗。风像在门缝里挤,像有人要从门缝里看。
凉生站在门后,掌心向下,轻轻一压:来。
她把手指按在他的指背上,也压了一下:来。
敲门声起。这次不急不慢的“笃笃”,三下,又三下。短、短、长。
门内的风铃轻轻响了一声,像在应。
她与凉生对视一眼,她把门闩按下,门开一指。
门外站着一个人,衣襟内侧绣了细边,指甲修得圆。月光照在他的脸上,他笑,笑里无笑:“娘子,补漏吗?”
她也笑:“补。”
风穿门而入,灯影在墙上晃了一下,像一只半羽的影,掠过去,又不见。